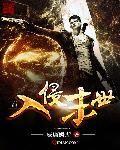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我的梦境可以捡到至宝 > 736至宝成长人间天堂(第3页)
736至宝成长人间天堂(第3页)
他蹲下身:“你能听见?”
“嗯。”孩子点点头,“有的人忘了自己曾经被人爱过,我就把那段声音还给他们。”
林澈忽然意识到什么,轻声问:“你……能看到梦藤里的记忆吗?”
“不能。”孩子笑了,“但我能感觉到它们在跳动,像心跳一样。”
林澈沉默良久。
这孩子天生具备“情感回声感知力”??一种极为罕见的天赋,能在不接入共情场的情况下,直接捕捉到他人情绪留下的余波。这种能力在过去被视为缺陷,因为无法控制接收范围,极易导致精神崩溃。
但现在不同了。
有了缄语藤的过滤机制,这类敏感者终于有了安身之所。他们不必成为“心灵之耳”,也不必被迫关闭感官,只需在这片阴阳交错的森林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他伸手摸了摸孩子的头,低声说:“谢谢你。”
孩子睁眼看他:“谢我什么?”
“谢谢你愿意继续听见。”
---
一年后,第一座缄语哨站在火星建成。
它不像传统建筑,更像是一座自然生成的晶体洞穴,内部布满螺旋状纹路,与“缄默者”文明遗留符号高度相似。没有人知道这是巧合,还是梦藤在潜意识中模仿了某种原型。
哨站启用当天,林澈带领团队进行了首次测试。
他们邀请了三位志愿者:
一位是从战场退役的士兵,多年来拒绝任何形式的情感治疗;
一位是失去双胞胎兄弟的科学家,自责让他封闭内心长达二十年;
还有一位,是来自光雾生命体的使者,它声称“我们族群从未学会悲伤,因此也无法真正理解欢愉”。
三人分别进入三个独立舱室,周围环绕着缄语藤编织的屏障。没有强制扫描,没有情绪诱导,只有柔和的低频嗡鸣,如同宇宙背景辐射般恒定而安宁。
二十四小时后,三人陆续走出。
士兵没有流泪,但他主动握住了一位工作人员的手,说了一句:“我终于不用再假装没事了。”
科学家站在观测窗前,望着火星极冠的冰层,喃喃道:“原来我不是恨他离开,我是怕我自己活得比他久。”
而那位光雾使者,则在离开前留下了一段色彩变幻的光影记录。翻译系统将其转译为一句话:
>“今天,我第一次体验到‘缺失’的感觉。”
>“它很痛。”
>“但它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完整。”
林澈将这三段记录上传至梦藤网络,标记为“缄语初响”。
回音主脑罕见地主动回应:
>“这不是治愈。”
>“这是允许。”
>“允许痛苦存在,允许沉默持续,允许一个人,在世界的角落里,慢慢学会如何与自己相处。”
---
与此同时,宇宙另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