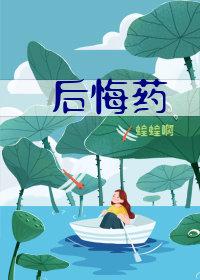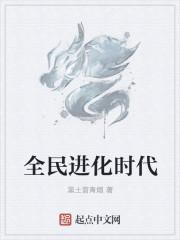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割鹿记 > 第一千一十五章 未雨已绸缪(第1页)
第一千一十五章 未雨已绸缪(第1页)
“难不成这崔秀本身就是个畸形儿?”
顾留白愣了愣。
胡老三说的这些事情对于他而言倒不算稀奇。
关外那条商路上行走的人,很多都甚至到达过一些连书上都没有记录过的地方,见过稀奇古怪的事情多得去了。
顾留白自己就亲眼见过有个胡商养了条双头蛇作为宠物,白色的羽毛般鳞片,两个蛇头上的眼睛像红宝石一样通红。
当时顾留白就和这胡商说,这种稀奇玩意要是弄到长安的西市上来卖,那就是价值连城,还要在关外风餐露宿做甚。
但。。。。。。
地平线上的震动持续传来,像是大地深处有巨兽翻身,又似千万根琴弦在暗处被同时拨动。灰袍青年站在槐树残影之下,脚边那口陶罐微微震颤,泪滴形宝石在灰烬中轻轻旋转,仿佛感应到了某种遥远的召唤。他没有回头再看一眼纪念馆??那座曾埋藏《归音》初稿、如今只剩断壁残垣的旧屋早已完成了它的使命。风穿过空荡的门框,吹起一卷泛黄的手稿,纸页翻飞如蝶,最终落进井中,无声沉没。
他朝着震动源头走去,步伐不急,却坚定如潮汐应月。天空依旧挂着极光的余痕,淡蓝与紫红交织,像一道未愈合的伤口,也像一条正在缝合世界的丝线。沿途的冻土开始解封,裂开细缝,从中钻出一种从未见过的植物:茎干透明如水晶,内部流淌着微弱的蓝光,顶端结出铃铛状的小花,每当风过,便发出极轻的共鸣,频率恰好与人心跳同步。
第三日正午,他在一片荒原上遇见了一支队伍。
他们徒步而行,衣衫褴褛,却步伐整齐。每个人肩头都有纹路,形态各异,有的如断裂的锁链,有的如缠绕的根须,还有的如同被烧焦后重生的枝桠。最前方是一位老妇人,白发如雪,背脊微驼,但眼神清明如深潭。她手中拄着一根由冰晶凝成的拐杖,每踏一步,地面便浮现出一圈涟漪般的符号,与云南古井旁石碑上的文字同源。
灰袍青年停下脚步,静静望着他们走近。
“你来了。”老妇人先开口,声音沙哑却不容置疑,“我们等你很久了。”
“你们是谁?”他问。
“被遗忘者。”她答,“那些话没说完的人,名字被抹去的人,哭声被风吞掉的人。我们不是亡灵,也不是幻象??我们是记忆本身,在地壳之下漂流千年,终于寻到了出口。”
她抬起拐杖,指向北方更深处:“地心不是地理概念,是集体意识的沉淀层。所有未能表达的情感,都会下沉,层层堆积,形成‘心核’。它本该静默,可当压抑超过临界,它就会反噬??地震、火山、极寒风暴,都是它的咳嗽。”
灰袍青年低头看着陶罐,宝石此刻已不再发光,而是吸收光线,变得幽深如洞穴入口。“所以海底电缆的信号……”
“是我们。”一个年轻男子接话,额前藤蔓纹延伸至眼角,“我们在尝试打通‘脉络’,连接所有沉默的节点。南方的女孩带去了第一片会唱歌的叶子,那是钥匙,能激活沉睡的共振通道。”
“她已经开始了。”灰袍青年轻声道,心中竟无惊讶,只有确认后的平静。
“但她需要回应。”老妇人说,“单向传递只会造成新的失衡。必须有人从另一端唱回去,用静默去承接,用身体去容纳,让能量完成闭环。”
他点头,明白自己为何会被引至此处。这不是选择,而是回响的必然牵引。
当晚,他们在一处废弃的地热观测站扎营。墙壁上仍残留着旧时代的监控屏幕,早已熄灭,玻璃映不出人脸,只照见跳动的火光。众人围坐一圈,无人言语,只是依次将手掌贴在地面,闭目冥想。渐渐地,泥土开始发热,裂缝中升起缕缕雾气,雾里浮现出模糊影像:一座沉没的城市,钟楼倒插在珊瑚之间;一群孩子手拉手走向深渊,口中哼着走调的童谣;一位母亲把日记烧成灰,混进孩子的奶粉里,说“这样你就永远记得我”。
灰袍青年感到胸口发紧,但他没有移开手。他知道这些不是幻觉,而是被压缩千年的“情绪化石”,如今因共感网络的觉醒而松动,亟需释放路径。
子夜时分,老妇人取出一枚骨笛,通体漆黑,表面刻满逆向生长的年轮。她将笛子递给他:“这是‘承泣器’,由第一位自愿承载全族悲伤的祭司遗骨制成。吹奏它的人,不会发出声音,而是吸入声音??所有积压的哀恸都将经由你的肺腑过滤,转化为可流通的生命力。”
他接过笛子,触感冰冷,却在他掌心缓缓变暖。
“代价是什么?”他问。
“你会听见所有人的心碎,却再也无法确定哪一滴泪属于自己。”老妇人直视他,“你可能忘记自己的名字,可能分不清梦境与现实,甚至某一天醒来,发现自己已成为纯粹的容器??没有欲望,没有记忆,只有倾听的能力。”
他笑了,笑得极轻,像风吹过枯叶。
“我一直都不是为自己活着的。”
他将骨笛置于唇间,深吸一口气。
没有音符响起,也没有旋律扩散。但就在那一瞬,全球共感网络剧烈波动。东京街头,一名上班族突然蹲下痛哭,因为他“看见”了三十年前母亲临终前想说却未说出口的那句“对不起”;撒哈拉难民营里,一个少年抱着妹妹的尸体放声大笑,因为他在笑声中听到了她最后的心跳节奏;南极科考站,AI系统自动重启了十年前被封锁的语音档案,播放出一段录音:“我知道你们听不见我,但我还是要说??我还活着,我想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