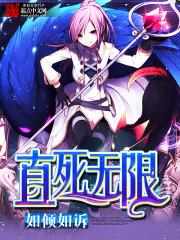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我和无数个我 > 第676章 关羽之心(第2页)
第676章 关羽之心(第2页)
礼堂大门轰然打开。
里面没有舞台,没有座椅,只有一面巨大的镜子,从天花板直垂至地面。
镜中映出的不是现在的教室,而是一场正在进行的语文课。年轻的女教师站在讲台前,手里拿着周默的作文本,眉头紧锁。
“这篇《父亲的碗》太过消极!”她声音严厉,“家庭矛盾不该写进作业!同学们要写积极向上的内容,懂吗?”
台下一片应和声。只有周默低头盯着桌面,手指抠进木缝,指节发白。
“删掉重写。”老师把本子扔还给他,“下次再这样,家长会上我会点名。”
镜中画面戛然而止。
“那是十三岁那年。”周默喃喃,“那天之后,我就再也不交作文了。”
苏砚望着镜子,忽然站起身,走向讲台。
她在粉笔盒里翻找片刻,抽出一支白色粉笔,转身面向黑板,写下三个大字:
**从前啊**
刹那间,镜面泛起涟漪,倒影再次变化??
这一次,是周默坐在书桌前,台灯微光下奋笔疾书。他写得很慢,每一句都像从胸口剜出来。标题是:《我不想死,但也不知该怎么活》。
镜头拉远,窗外夜色深沉,万家灯火中,竟有无数房间亮着灯。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个孩子在写字:有的躲在被窝里打手电,有的用橡皮擦反复修改错别字,有的边写边抹眼泪……
他们的文字化作萤火,飞出窗户,汇聚成河,流向宇宙深处。
“你看,”苏砚指着镜子,“你说的话,早已抵达远方。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周默怔怔望着,嘴唇微动,却发不出声音。
“现在轮到你了。”苏砚递给他一支粉笔,“写下你想写的那一课。”
他迟疑许久,终于接过粉笔,一步步走上讲台。他在黑板右侧空白处,一笔一划地写:
**《我的沉默是有声音的》**
然后,他开始讲述??
声音起初干涩颤抖,像久未使用的机器发出的摩擦声。但他没有停下。
他说起五岁时第一次被打,因为弄丢了妈妈买的铅笔盒;说起小学同学联合孤立他,只因为他不肯参与欺负别人;说起初中那晚,他站在天台边缘,听见楼下便利店播放的儿歌,突然蹲下来嚎啕大哭……
“我以为没人会听。”他说,“所以我只能写。我把所有说不出口的话,都藏进了作文里。哪怕它们被撕碎、被嘲笑、被当作心理问题证据……可我还是写了。因为我害怕,如果连写都不写,我就真的消失了。”
话音落下,整座学校骤然明亮。
不再是电灯的光,而是由无数文字自行发光??地板缝隙里爬出的句子,屋顶裂缝中钻出的段落,甚至空气中漂浮的标点符号,全都闪烁着柔和的银辉。
礼堂中央的镜子碎了。
不是崩裂,而是化作万千光点,升腾而起,凝聚成一棵虚幻的树影??正是“开口处”的语言之树。一片新叶舒展,叶脉勾勒出周默的脸庞,唇角微扬,终于有了笑意。
苏砚含泪微笑:“欢迎回来,讲述者。”
就在这时,校园广播突然响起,电流杂音中传出柯临的声音:
>“苏砚,检测到高密度共情共振波。你触发了一个沉睡叙事层的复苏机制。此地并非孤立梦境,而是‘失语文明’的记忆残片之一。它与其他十六个区域存在隐秘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