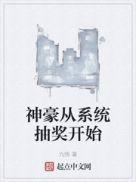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春色满棠 > 第492章 路线本殿下都给你们画好了(第3页)
第492章 路线本殿下都给你们画好了(第3页)
第一课:认识自己的名字。
请各位同学,在纸上写下你的名字。不要怕写错,不要怕笔画歪斜。这个名字,是你出生时父母的期盼,是你活在这世上的凭证,是你对抗遗忘的第一道防线。
如果你的母亲没留下名字,请写下你记得的她的样子;
如果你的祖母一生被称为‘某氏’,请你替她补上姓氏;
如果你曾被人说‘女娃不必有名’,今天,请你为自己正名。
写好了吗?好,现在,请大声念出来??
我叫__________,
我活着,
我有声音,
我在这里。”
录音结束,山谷寂静。
片刻后,远处传来孩童的歌声。那是回声谷小学的孩子们,在排练新编的《识字娘子军》合唱曲。歌声清澈,随风飘来:
>“一横是天,一竖是地,
>撇捺之间,站起一个你。
>不依附,不低头,不沉默,
>我的名字,我自己写。”
林小禾走出校门,看见陈砚站在海棠树下等她。他手里拿着一封信,是从台湾寄来的,沈云岫孙女的新信。
“她说,祖母的日记原本有两本。”陈砚展开信纸,“第二本一直锁在家族保险柜里,最近才找到。里面记录了1951年冬天,她和几位女教师徒步穿越雪岭,为偏远山寨送课本的经历。途中遭遇暴雪,一名同伴坠崖身亡。她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带的不是书,是命。她们若不识字,就会一辈子被人当成死物。而我们要做的,是让她们复活。’”
林小禾接过日记复印件,指尖微微发抖。
“她还说,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你们教材的一部分。”
“会的。”林小禾轻声道,“我们要把它编进‘女性教育史’课程,让每一个新学员都知道??这条路,从来不是一个人走的。”
暮色四合,新建的夜校亮起灯火。第一期学员即将报到,报名人数远超预期:837人,来自全国28个省份,最小的16岁,最大的91岁。她们中有留守农妇、进城务工者、残疾人士、单亲妈妈、退休职工……每个人都在申请表上认真写下同一句话:“我想学会写自己的故事。”
当晚,林小禾伏案工作至深夜。她在《回声集》第二辑的序言中写道:
>“有人说我们太理想主义。可当我看到一位七十岁的老人,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句朗读《宪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时眼里的光;
>当我听到一位盲女通过语音APP第一次‘读’完一首诗后笑着说‘原来文字是有温度的’;
>当我收到无数封署名‘某某本人’的来信,而不是‘某妻’‘某母’??
>我就知道,理想不是虚妄,而是尚未实现的真实。
>
>我们不做救世主,只做点灯人。
>灯一旦亮了,就不会再熄灭。”
窗外,海棠花瓣悄然飘落,沾在她的稿纸上,像一枚枚粉色的印章,见证着这场静默而壮阔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