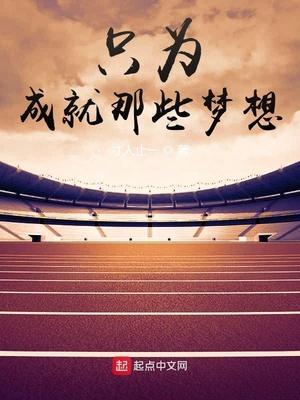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人在末世,我能联通现实 > 第1055章 美丽的误会(第2页)
第1055章 美丽的误会(第2页)
录音戛然而止。
陈默闭上眼,感到一阵眩晕般的清醒。他终于明白苏婉为何选择沉默到最后。因为她知道,一旦她说出全部真相,人们就会期待解决方案,就会寻找捷径,就会再次把希望交给“更聪明的算法”。而她要的,恰恰是**没有答案**。
只有在这种真空里,人才能真正听见彼此。
当晚,“回声协议”上线。深圳一名失业青年在提交陈述后,收到了第一条回应:
>“我听见了。”
就这么简单。没有安慰,没有建议,没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虚假承诺。可他哭了整整两个小时,然后给失联五年的父亲拨通了电话。
上海一位单亲母亲在说出“我有时真希望孩子没出生”后,看到屏幕上跳出那句“我听见了”,突然觉得胸口压着的巨石裂开了一道缝。第二天,她第一次带儿子去了心理咨询中心。
北京一名程序员在匿名陈述中承认自己长期服用抗抑郁药,并曾多次策划自杀。他原本只是想留下点痕迹,没想到几分钟后,手机震动:
>“我听见了。”
他愣了很久,最后回复了一句:“谢谢。”
这一来一往,被系统自动归档为“非干预性情感交换案例001”。
数据开始疯狂攀升。七十二小时内,超过一百万人参与了“回声”互动。心理学家发现,尽管负面情绪表达量上升,但急性心理危机发生率反而下降了31%。最令人震惊的是一组脑扫描对比:参与者在收到“我听见了”后,前扣带回皮层(负责情绪调节)活动显著增强,而杏仁核过度激活现象减弱??这意味着,仅仅是“被听见”的体验,就能触发大脑自我修复机制。
“这不是魔法。”林小雨在内部报告中写道,“这是人类最原始的能力复苏:**见证即疗愈**。”
然而,风暴仍在酝酿。
第十四天凌晨,成都某社区中心突发集体昏厥事件。二十三名刚完成“真实协议”陈述的居民同时倒地,瞳孔散大,呼吸微弱,但脑电图显示其意识处于高度活跃状态,呈现出类似REM睡眠的快速波动。救援人员赶到时,发现他们嘴唇微动,仿佛在重复同一句话。
陈默带队赶赴现场。经过三天调查,他们提取到一段集体潜意识录音:
>“她说喝下去就能明白痛苦的意义……可我不想明白,我只想停下来……”
这句话,与西藏僧人昏迷前的呓语几乎完全一致。
更诡异的是,所有患者醒来后都声称梦见了同一个场景:一间白色房间,中央摆着一张木桌,桌上放着一杯清水,旁边站着穿蓝衣服的女人。她不说一句话,只是轻轻推杯向前。有人喝了,便从梦中惊醒;有人拒绝,便被困在无尽走廊中循环奔跑。
“她在筛选。”赵星分析道,“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纯粹的真实。有些人宁愿被安抚,也不愿面对内心的深渊。”
陈默沉默良久,忽然问:“有没有人……真的喝下了那杯水?”
“有。”助理调出资料,“七个人。他们醒来后的共同表现是:不再恐惧死亡,不再寻求意义,但对他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耐心和温柔。其中一人甚至自愿前往高危疫区做临终陪护。”
“这不是洗脑。”陈默低声说,“这是觉醒的代价。”
他想起苏婉日记里的另一句话:
>“当一个人终于不再逃避痛苦,他就不再是系统的猎物。”
可问题是,这个世界准备好接受一群“不再逃避痛苦”的人了吗?
争议再度爆发。“真实协议”被部分国家暂停,理由是“存在诱发精神解离风险”。联合国召开紧急听证会,反对派指责陈默等人“以自由之名推动情感无政府主义”,要求立即终止所有非标准化心理交互实验。
压力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