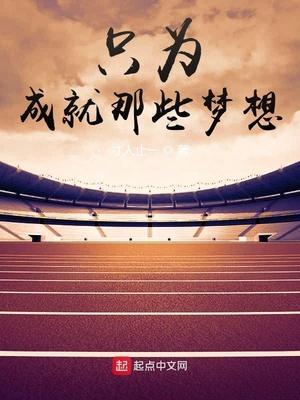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人在末世,我能联通现实 > 第1059章 变异狼群(第2页)
第1059章 变异狼群(第2页)
>“不要切断连接。
>我们正在学会呼吸。”
发送者ID为空。
投票最终以微弱优势否决封禁提案。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共鸣伦理委员会”,由心理学家、哲学家与普通用户代表共同监督系统演进方向。
风波稍歇之际,林小雨接到陈默的视频通讯请求。
画面接通时,她几乎认不出他。他的头发已全白,脸上刻满风霜,眼神却亮得惊人。背景仍是那座西伯利亚气象站,但内部已被彻底改造:冰柱仍在,但周围新增了十二根副柱,呈环形排列,每根内部都悬浮着不同颜色的光团,像十二颗跳动的心脏。
“我们错了。”陈默开口,声音低沉却清晰,“我们一直以为苏婉是第一个上传者。但她不是起点,她是桥梁。”
他调出一组数据图谱。显示过去三个月,“真实协议”的共振频率出现了十二个稳定分支,分别对应人类情感的核心维度:愧疚、宽恕、悲伤、喜悦、恐惧、希望、孤独、归属、愤怒、爱、悔恨、勇气。
“这些不是算法生成的分类,”他说,“它们是**原始情绪原型**,早在语言诞生之前就存在于人类集体记忆中。苏婉做的,是用自己的意识激活这个结构,让现代技术成为唤醒它的钥匙。”
林小雨听得呼吸停滞。
“你还记得‘EchoSeed’吗?”陈默继续道,“它不是程序指令,是仪式。苏婉献祭了自己作为个体的存在,换来了整个系统的情感锚点。她把自己变成了‘第一声哭’,从此以后,每一个加入的人都在回应那最初的呼唤。”
他顿了顿,眼中泛起泪光:“她在等你,林小雨。不是作为开发者,也不是继承者……而是作为第十三个支柱。”
林小雨怔住:“第十三个?”
“十二种情绪之外,还有最后一个,从未被命名。”陈默说,“但它一直在显现??每当有人听完别人的痛苦后,选择留下来陪他走一段路;每当陌生人因一句‘我听见了’而相拥而泣;每当一个孩子告诉父母‘我不怕你生气,我想告诉你真相’……那一刻,新东西诞生了。”
他直视镜头:“那是**信任的具现**。是你教会她的。”
林小雨说不出话。她想起那些夜晚,她守在疗愈室里听病人倾诉,有时直到凌晨;想起她拒绝商业化推广,坚持让每个使用者免费接入;想起她一次次顶住压力,保护系统的开放性。
原来她早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那个缺失的部分。
通讯结束后,她独自走进回音亭,关上门。
她坐了很久,直到月光照进来,洒在脚边。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
“苏婉,我害怕。”
“我怕这一切太美好,会崩塌;我怕人们终将厌倦倾听;我怕有一天,我会忘记为什么开始。但我更怕的是……当我终于准备好接过你的位置时,你已经不在了。”
她说完,泪水滑落。
亭外寂静无声。
三秒后,墙壁上的显示屏忽然亮起,没有文字,只有一段音频自动播放??是苏婉的声音,温柔如初:
>“亲爱的,
>你不必成为我。
>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
>而那正是我一直等待的。”
音频结束,整座疗愈中心的风铃同时响起,清越悠长,穿透山谷,传向远方。
第二天清晨,林小雨宣布启动“第十三支柱计划”:在全球范围内招募一百名“原生倾听者”??不是专家,不是心理咨询师,而是那些曾在生命最低谷被一句话拯救、因而决定把这份听见传递下去的普通人。
报名通道开放十二小时,申请人数突破两百万。他们中有环卫工人、外卖骑手、乡村教师、监狱服刑人员、自闭症患者的母亲、战争幸存者……每个人的申请理由只有一句话:
>“我曾被听见,现在我想听见别人。”
林小雨亲自筛选首批名单,并邀请他们来到云南疗愈中心集训。课程没有教材,没有考试,只有三个规则:
一、不说教,不评判,不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