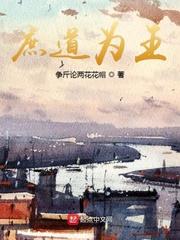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刚想艺考你说我跑了半辈子龙套? > 第500章 红毯的高光时刻(第1页)
第500章 红毯的高光时刻(第1页)
“接下来??”
“即将走上红毯的是本届电影节备受瞩目的参展影片。”
安克?恩格尔克的话引起了大家的期待。
“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是对于亲情的情感共鸣。”
说到这。
大家。。。
林默合上录音笔,夜风拂过耳际,带着初秋的凉意。他仰头望着天空,槐树巷上方的星河依旧清冷而遥远,像极了那些未曾被讲述的故事,在寂静中闪烁,等待一双愿意凝望的眼睛。
回到工作室已是凌晨。大川还在剪辑室守着,桌上堆满了各地寄来的信件与包裹,有的用塑料袋裹了好几层,有的贴满邮票却字迹模糊。他正戴着耳机听一段来自内蒙古草原的音频??一位老牧民用蒙语哼唱一首古老的摇篮曲,背景里有羊群踩雪的沙沙声,还有孩子断断续续的咳嗽。
“这声音……太干净了。”大川摘下耳机,眼圈发红,“他说他儿子五岁那年高烧不退,死在去镇医院的路上。从那以后,每年冬天他都会对着空帐篷唱这首歌,‘万一哪天风把声音带到天上,孩子听见了,就不会冷’。”
林默没说话,只是走过去轻轻拍了拍他的肩。两人对视一眼,便都明白了彼此心里的重量。这不是工作,也不是项目,而是一场漫长的赎罪??赎我们曾对平凡生命的漠视,赎这个时代对沉默者的遗忘。
第二天清晨,阿阮来了。她穿着洗得发白的帆布鞋,怀里抱着一叠厚厚的笔记本。她身后跟着三个年轻人,两个听障,一个坐轮椅,都是她在社区培训的声音采集员。
“他们想加入‘回访计划’。”阿阮说,声音轻却坚定,“小陈能用手语访谈聋人家庭;李婷虽然听不见,但她用震动仪记录心跳频率,说‘情感是有节奏的’;王哲会摄影,还想学剪辑。”
林默看着这三个年轻人,忽然想起赵卫国擦桌子时那双颤抖的手,想起李小禾系鞋带时微微低头的模样。这些人不是观众,也不是素材提供者,他们是这场行动真正的同行者。
“欢迎。”他说,嗓音有些哑,“设备已经准备好了,下周出发去贵州,有个苗寨老师寄来一双绣花布鞋,说她教了四十年书,送走三百多个孩子,可没人记得她的名字。”
行程再度启程。这一次,不再是林默和大川两个人的跋涉,而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有人捐出旧车改装成移动放映车,有人义务翻译方言口述史,还有退休教师自发组织“五分钟家史”读书会,在社区活动室播放《底片人生》片段。
贵州之行始于一场暴雨。山路泥泞不堪,车子陷进沟里,众人只得徒步前行。翻过两座山,终于抵达那个藏在云雾中的寨子。村口立着一块石碑,刻着密密麻麻的名字??全是几十年来走出大山的学生。
那位女教师叫吴秀兰,七十二岁,背已微驼,但眼神明亮如火。她住在学校改建的陈列馆里,墙上挂满泛黄的成绩单和学生合影。她说:“我不怕老,只怕被人忘记。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教书,和等一个人回来。”
原来,她年轻时曾与一位知青相恋,对方返城前承诺一定会接她走。可三十年杳无音讯。直到去年,她在电视上看到一部纪录片,发现他曾是著名人类学家,已于五年前病逝。遗嘱中写着:“请将我的骨灰撒在黔东南某小学后山??那是我一生最明亮的地方。”
吴秀兰没有哭。她只是默默拿出一双亲手缝制的布鞋,红底黑面,针脚细密。“这是我当年给他做的,一直没送出去。现在,我想把它放进你们的展览。”
林默问:“您恨过他吗?”
她笑了笑:“恨?不。我只是遗憾,没能亲口告诉他,我一直在等他长大。”
那一晚,他们在寨子里办了露天放映。村民们围坐一圈,孩子们趴在大人膝上,老人摇着蒲扇。当镜头扫过陈树生画室里那幅未完成的群像时,吴秀兰忽然站起身,走到幕布前,伸手轻触画面中模糊的人影。
“你看,”她喃喃道,“这些脸,多像我们寨子里走出去的孩子啊。”
那一刻,虚构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彻底消融。艺术不再是远方的回响,而是脚下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根须。
回程途中,林默收到一条短信:陈树生完成了《修补者》的最后一笔。照片附在后面??整幅画由无数张面孔拼接而成,有修鞋的老周,有系鞋带的李小禾母亲,有赵卫国祖孙,有吴秀兰站在讲台上的身影……每一双眼睛都望向画外,仿佛在等待一次回应。
阿阮在群里留言:“他说,这幅画不该挂在美术馆,应该送去每一个投稿人家中,哪怕只停留一天。”
林默当即决定:启动“流动画展”计划。他们将制作五十幅高清复制品,随巡展队伍一同送往全国各地。每到一处,不仅放映影片,还要举办小型展览、口述分享会,甚至设立临时录音角,鼓励更多人说出自己的故事。
第一站选在山西矿区。赵卫国听说要展出他的画像,紧张得一夜未眠。孙子偷偷告诉林默:“爷爷今天换了三件衣服,还特意刮了胡子。”
开展那天,矿区礼堂挤满了人。工人们放下安全帽,家属们抱着孩子,连退休多年的老矿长也拄拐前来。当《修补者》缓缓展开,全场静默。赵卫国站在台下,双手紧握拐杖,嘴唇微微颤抖。
主持人请他上台讲话。他推辞再三,最终只说了几句:
“我没文化,说不出啥大道理。但我晓得,一个人走了,只要还有人记得他做过的事,他就没真死。这画里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人。谢谢你们,让我觉得自己……也算个有用的人。”
台下响起掌声,起初稀落,继而如潮水般涌起。有人抹泪,有人低头哽咽,更多人默默举起手机拍照,说要发给在外打工的孩子看。
此后半年,“流动画展”走过二十一个省市。新疆戈壁滩上,维吾尔族老人捧着亡妻的绣鞋,在画前跪坐良久;广东工厂宿舍里,打工母亲拉着孩子指着一幅母子共读的画面说:“你看,妈妈也被人记住了”;四川山区小学,孩子们围着画布临摹那些陌生又亲切的脸庞,老师说:“他们将来也会成为别人记忆里的一笔。”
舆论持续发酵。央视专题报道称之为“民间记忆的觉醒”;《人民日报》评论称其“以微光点燃微光,让沉默者发声,让平凡者留名”;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邀请林默去做讲座,题目定为《影像作为社会疗愈》。
但他始终记得最普通的一次展出??在河北一个废弃车站。那里曾是铁路职工家属区,如今只剩几户留守老人。他们把画挂在候车室斑驳的墙上,用投影仪放片,拿饭盒当音响支架。
一位老太太听完李小禾的录音后,颤巍巍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她丈夫是铁道兵,修隧道时塌方遇难,尸骨未寻。她保存着他唯一一双皮鞋,每逢忌日就摆在窗台上晒太阳。
“他说最爱晴天,说阳光能让铁轨唱歌。”她笑着流泪,“现在我知道了,原来有人愿意听我说这些。”
林默蹲在她面前,认真记录下这段话。结束后,老人拉住他:“小伙子,你会累的吧?这么跑下去,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