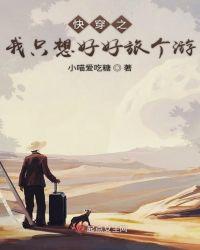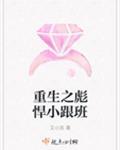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沈小姐今年40岁(韩娱同人) > 地下美人(第1页)
地下美人(第1页)
沈嘉鱼多年前在戛纳遇见过一个女演员,她很有天赋,是当之无愧的天才演员,她拍过很多很精彩的作品,可惜奖运不太好,这么多年一直没拿过主流大奖。没有奖杯并不会导致你在娱乐圈混不下去,有奖杯也不意味着你就掌握了话语权,只不过演技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观众很难比较不同演员表演间的细微差距,所以他们选择用奖杯来判断,谁拿奖更多,谁就更权威,就像群众总是会盲目选择专家,相信他们的发言就是最正确的。
沈嘉鱼欣赏那位女演员,但从未想过要成为她那样的人,清高、自傲的艺术家适合出现在电影里,而不是电影圈。沈嘉鱼对自己的演技很自信,但她也清楚如果没有公司精心的运作,恰到好处的公关,自己很难实现影后大满贯。娱乐圈是一个巨大的名利斗兽场,天赋是入场券,野心和手段才是通往领奖台的阶梯,她不想做那个被后人唏嘘感慨“遗珠之憾”的天才,她要做就做那个站在聚光灯下,手捧奖杯,接受仰望的人。几十年后,谁会继续在意媒体对获奖结果的非议,历史只会记录最后的结果,当年的新闻报道早已无人关注,民众只会夸奖影帝影后们为国争光。
沈嘉鱼想不清楚未来的方向,她决定去江原道找元斌聊聊。沈嘉鱼开车前往江原道的路上,窗外的景色从高楼大厦过渡到绿意盎然的田野,最后变成海边无垠的蔚蓝。她需要这种物理上的抽离,来厘清脑子里那团乱麻。韩国电影市场的低迷像一盆冷水,浇熄了她在威尼斯封后之后一路高歌猛进的势头。国内的奖杯拿够了,再拿也只是重复,意义不大,而更上一层楼,去触碰戛纳、柏林乃至奥斯卡的王冠,对于一个亚洲女演员来说,希望实在渺茫。那道鸿沟不是光靠野心和运作就能填平。她选择将事业重心转移到电视剧上,开始尝试与网飞合作,可网飞递来的剧本不是政治,复仇就是犯罪,雷同到像是同一条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一样。
元斌坐在海边的咖啡厅等她,他们随意地聊起这些年的故事,聊起共同认识的熟人,谁又拿了奖,谁转了型,谁渐渐地没了声音……沈嘉鱼忍不住问他有没有后悔错过了韩娱蓬勃发展的这几年,东方资本涌入,西方平台布局,这是韩国演员前所未有的机遇期。元斌听完,只是淡淡地笑了笑,“我只是扮演过‘元斌’的演员金道振而已。‘元斌’这个名字,已经不需要其他更多东西来证明了。它本身,就是一个招牌。”元斌选择在巅峰期隐退,用绝对的抽离,将“元斌”这两个字固定在了传奇的位置上。他没有被过度消费,没有在烂片里消耗口碑,他的形象在公众记忆里永远是完美的,带着神秘感和距离感。这是一种更高级的,以退为进的“经营”。沈嘉鱼一直追求的,是不断用新的奖杯、新的角色来维护自己的权威,证明自己的“在场”。而元斌用“缺席”成就了另一种永恒。这不分对错,只是选择的不同。
回程的路上,沈嘉鱼的心情不像来时那般沉重。元斌的话点醒了她,文艺片冲奖这条路已经不再适合当前的韩国电影市场,网飞的模式虽然让她审美疲劳,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是全球发行的网络平台,能帮她实现自己的商业价值;又或者,她可以继续等待,寻找那个真正适合她的剧本。
虽然她的事业暂时停滞,但至少,她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往哪个方向试探了。沈嘉鱼不愿成为被时代裹挟向前的浮木,也不想困在昔日荣光里,前路依旧未知,但至少方向盘在她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