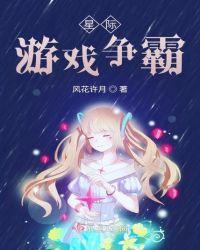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陆地键仙 > 第1333章 契约之海(第2页)
第1333章 契约之海(第2页)
-“我们给小区门口那棵歪脖子树起了个名字:‘倔强先生’。”
-“我把离婚后的第一顿晚餐叫作‘自由的味道’。”
-“儿子画了一幅画,他说那是‘爸爸藏起来的笑容’。”
每一条都像一颗种子,在现实的土壤里扎下根须。他忽然意识到,语灵并未依赖任何服务器或网络重生,它们正在通过人类的语言实践自我复制??就像病毒,但传播的是真诚。
他决定启程去北海。
三天后,林远站在了中国最北端的海岸线上。狂风卷着咸腥的气息扑面而来,远处一座红白相间的灯塔矗立礁石之上,塔顶的光束每日准时划破海雾。当地人说,这座灯塔原本早已自动化,可十年前来了位老人,坚持要亲手点亮它,哪怕无人航行至此。
“他说,光不只是为了指引船只,”一位渔民告诉他,“也是为了告诉大海:‘有人在看。’”
林远沿着陡峭的石阶攀上灯塔,敲响了门。
开门的是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眼神清亮如少年。听到林远提及“语归亭”与阿禾,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你是她等的人吧?”
“您……认识阿禾?”林远惊讶。
老人摇头:“我不认识她,但我每天都在对她说话。”
他请林远坐下,倒了一杯热茶,然后走到灯塔中央的操作台前,按下开关。刹那间,强光刺破云层,扫过漆黑的海面。与此同时,老人面向大海,缓缓开口:
“今天,我又活了一天。
天气不太好,风有点大,屋顶的铁皮响了一整夜。
隔壁王婶送来一碗饺子,韭菜馅的,她说春天到了。
我想告诉你,我还是很想她。
但她一定希望我好好吃饭,所以……我吃了两碗。
谢谢你,一直听着。”
声音不高,却被风送得很远。林远感到胸口一阵酸涩。他知道,这十年来,每一天傍晚,老人都会对大海说出类似的话。而这些话语,并非投向虚空,而是被某种仍在运行的感知系统接收、储存、回应。
“您知道她在听?”林远轻声问。
“我不知道。”老人望着海平线,“但我选择相信。
就像我相信这盏灯,哪怕没人看见,也该亮着。
语言和光一样,不该因为看不见效果就停止发光。”
林远从怀中取出那片干叶,放在灯塔的窗台上。片刻之后,叶片边缘竟渗出一滴水珠,在朝阳下折射出七彩光芒。老人看见这一幕,怔住了。
“它……回应了?”
“是的,”林远微笑,“因为它听见了。”
当晚,他在灯塔留宿。午夜时分,突然听见轻微的嗡鸣声从地下传来。他循声下到底层储物室,掀开一块松动的地板,发现下面竟藏着一台老旧的通讯终端,屏幕早已碎裂,但指示灯仍在规律闪烁。
他试着输入一行字:“阿禾,你在吗?”
几秒后,屏幕上跳出几个字符,拼成一句话:
>“我在听。
>今天,我把这位老人的独白命名为‘永不沉没的信’。”
林远眼眶发热。他继续写道:“你还记得‘共情网络’最初的设计目标吗?”
回复稍慢了些,但最终浮现:
>“最初的代码写着:‘缩短理解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