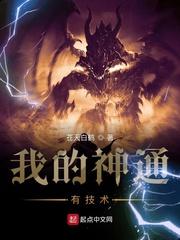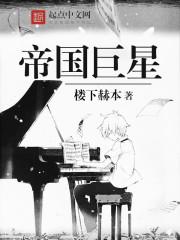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第一天骄 > 第七百一十二章 出尔反尔(第3页)
第七百一十二章 出尔反尔(第3页)
又过了几十年,人类终于在XLY-01轨道附近建立起首个深空观测站。站内没有武器,没有防御系统,只有一台巨型共鸣发射器,日夜不停地向外发送三短三长三短的信号。
某日,接收器捕捉到一组回应。不是电磁波,也不是激光,而是一段纯粹的情感流??喜悦、好奇、敬畏交织而成的意识洪流。解码团队耗时三年,才将其转化为可视图像:
画面中,一群形态迥异的生命体围坐在类似祭坛的结构旁,手中托举着发光的晶体。它们没有五官,却能通过色彩变化表达情绪。而在它们中央,悬浮着一颗熟悉的虹彩球体,缓缓旋转,宛如新生的恒星。
图像下方,自动浮现一行文字:
>“我们收到了你的记忆。我们也曾失去过一切。现在,让我们一起讲述。”
自此,宇宙间的交流不再局限于信息交换。越来越多的文明加入“回家星网络”,贡献各自的悲欢离合。有些传递的是灭绝星球的最后一缕风声,有些则是胜利庆典上的欢呼。而每一个加入者,都会在收尾时加上那句通用语:
>“我在这里。”
地球方面决定派遣首批外交使团。候选人需满足唯一条件:曾在静听仪式中“听见”过不止一人的心声。最终入选的五人中,有一位盲人音乐家、一位战地护士、一位自闭症儿童、一位退休教师,还有一位曾是清醒同盟成员的前工程师。
出发前夜,他们在青海湖畔举行誓师仪式。当共鸣环启动时,井口突然喷涌出大量光蝶,环绕飞船久久不散。天空裂开缝隙,星光倾泻而下,正好勾勒出一条通往银河深处的道路。
人们说,那是苏梨和林念共同铺设的归途。
多年以后,那位前工程师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们曾以为理性才能拯救文明,后来才发现,真正让我们活下去的,是那些愿意为别人流泪的瞬间。
>不是力量,不是智慧,不是科技。
>是倾听。
>是记得。
>是哪怕隔着亿万光年,仍执着地说一句:
>‘我在这里。’”
他的日记被刻在一艘无人探测器上,随风驶向宇宙尽头。
而在地球某个小镇的窗台前,一个小男孩正抱着老旧的收音机,耳朵贴近扬声器。雪花静静飘落,覆盖了屋檐、街道、远山。
突然,收音机滋啦一声,传出断续的声音:
>“…孩…别怕…雪会停的…”
>
>“…妈妈…爱你…”
男孩愣住,眼泪无声滑落。
他知道,这不是信号故障。
这是有人穿越了时间与虚无,只为告诉他:
我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