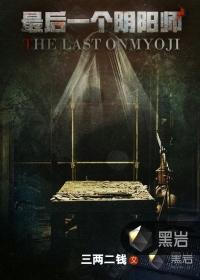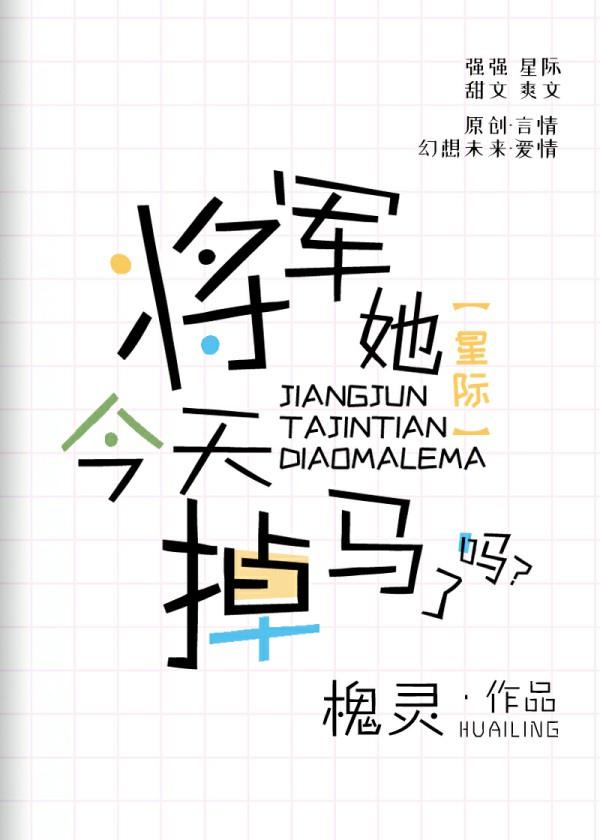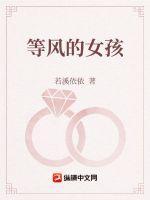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挟明 > 第七五六章 夜驰急马蹄(第2页)
第七五六章 夜驰急马蹄(第2页)
两名“鸣铎者”同时出手,一人吹笛定音,另一人迅速打开随身携带的小型共鸣箱,释放出预先录制的标准《韶乐》片段。两股正声交汇,如同阳光照进阴窟,瞬间瓦解了邪音的控制力。
全场骤然清醒。
寒潭子面色剧变,猛地拂袖断弦,欲逃。却被早已埋伏的暗卫擒住。搜身所得,除了一枚刻有“南烛奉祭”的玉佩外,还有一本手抄乐谱,封面写着《逆韶?九殇篇》,其中详细记载了如何利用特定频率诱发群体性悲伤与绝望情绪。
此案震动江南士林。原本对工正新政持保留态度的文人纷纷表态支持,认为“音乱则心乱,乐正则政通”。就连一向谨慎的赵文藻也不得不承认:“你这一手,比查案更有效。”
然而李延年知道,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因为就在审讯寒潭子当晚,他在牢中自尽,嘴角含笑,留下一行血书:“井将闭,灯将熄,天命不可违。”
几乎同一时间,云南大理传来急报:洱海湖底一夜之间浮现出七块巨石,排列成北斗之形,每块石头表面都刻着半个音符。专家拼合后发现,这竟是《韶乐》终章缺失部分的残谱,但旋律走向诡异莫名,既非宫商角徵羽,也不合十二律吕,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响。
李延年亲赴大理勘察。站在湖边高台上,望着水中星石倒影,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礼曹的目的从来不是简单地复活旧乐,也不是仅仅建立新秩序。
他们在尝试**沟通某种存在**。
一种藏于地脉深处、借音波为媒介的古老意识。或许就是古人所说的“地?”,或是《山海经》里记载的“穴帝”。而“八祭”不过是献祭仪式,“井字格局”则是召唤阵法,最终目标,是在人间打开一道通往“幽音界”的门。
难怪他们需要“共鸣体”??不仅要懂音乐,更要具备足够的精神强度,才能承受那扇门开启时的冲击。
而他自己,恰恰是最理想的容器。
这个念头让他脊背发凉。
但他没有退缩。
回到昆明后,他下令封锁洱海区域,并秘密召集三位顶尖工匠,按照祖父李维周遗留的设计图,打造一口前所未有的钟??它不再只是发声工具,而是一座“心灵锚点”。钟体采用纯锡青铜铸造,内壁镌刻整部《工正启蒙读本》,外缘环绕十二律母纹。最关键的是,钟舌并非固定,而是悬浮于电磁场中,只有在演奏者心志坚定、意念纯净时,才能触发真正完美的共振。
这口钟,名为“守志”。
启用之日,李延年亲自执槌。
第一声响起时,整个昆明盆地的鸟群同时腾空;第二声过后,千里之外的南京明孝陵石碑上,那被涂黑的《韶乐》终章竟隐隐泛出微光;等到第九槌落下,洱海湖底的七块星石齐齐震颤,随即沉入深渊,再未出现。
从此,每逢朔望之夜,“守志钟”都会鸣响三次,声波经由特殊介质传导,覆盖全国所有工籍登记点。凡持有工牌者,无论身处何地,都能感受到那一瞬的清明震荡,仿佛灵魂被轻轻擦拭。
十年过去,社会风气悄然改变。人们说话更加坦诚,争执减少,甚至连犯罪率都显著下降。学者们称之为“音频教化效应”,而百姓只说:“听钟之后,心里亮堂。”
可李延年知道,敌人并未消失。
某年中秋,他巡视西北,在敦煌莫高窟某间封闭已久的唐代乐舞窟中,发现一幅壁画残片:画中九人围坐地穴四周,手持奇形乐器,中央一人仰首向天,口中喷出无数音符,直冲北斗。题记仅存两字:“**召启**”。
而在洞窟最深处,一块石板下压着一封密封陶函。打开后,里面是一卷羊皮地图,标注了全国九十九处“声眼”位置,其中三十七处已被标记红点,旁边小字注明:“继明塔将立,速改布局。”
最后一行写道:
>“我们不在暗处,我们在你们听不见的地方。”
李延年静静看完,将地图投入烛火。
火焰升起的刹那,他仿佛听见远方传来一阵极细微的笑声,像是风吹过断裂的琴弦,又像某个人正在轻轻哼唱一首还未完成的歌。
他闭上眼,低声回应:
“你们可以藏在无声之处,但只要还有人心记得光明,我就一定能找到你们。”
翌日清晨,“继明钟”车队再度启程,驶向下一站??甘肃武威。
车上新增一面旗帜,上书四个大字:
**声之所向,心之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