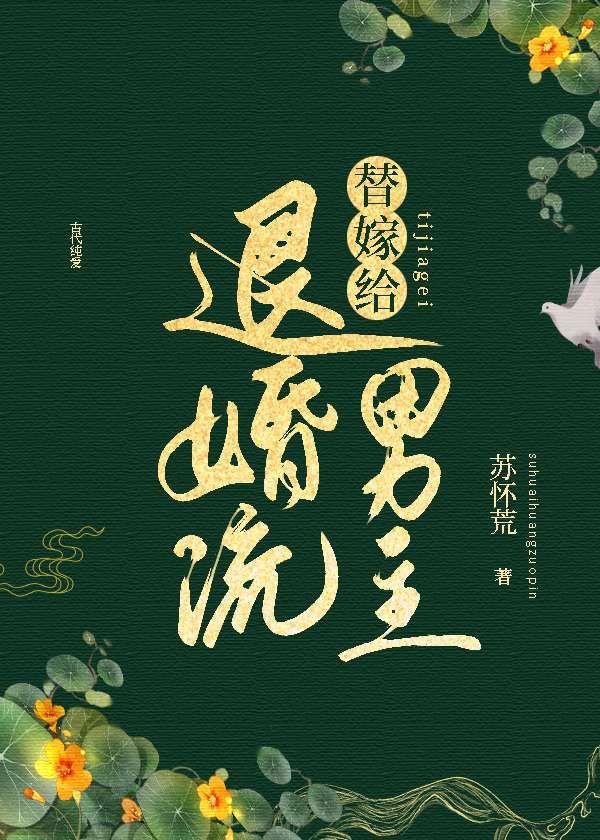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夫人请住口 > 第344章 少年得志者满堂文曲星求月票(第3页)
第344章 少年得志者满堂文曲星求月票(第3页)
>不是消除差异,
>而是让差异发出声音。
>不是追求理解,
>而是允许不被理解。
>当你说出‘我不懂你’,
>却仍愿意听下去,
>那一刻,
>桥已建成。”**
台下,万人静默,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有人欢呼,有人跪地痛哭,有人紧紧抱住身边的人,仿佛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
我站在人群中,忽然感到一阵熟悉的震动。低头一看,碎晶在我的掌心发烫,光芒流转,竟与心脉图产生了共振。紧接着,耳边响起一段旋律??是我父亲的渔歌,但这一次,歌词清晰可辨:
>“海不言,却知潮汐;
>风不语,却送归帆。
>若你问我爱不爱你,
>看那浪花一遍遍扑向岸,
>那就是答案。”
我浑身一震。这不是记忆,是传承。父亲的歌声,母亲的沉默,我的呐喊,千万人的低语……全都汇入了这同一段旋律,成为渊语的一部分。
当晚,我独自回到海边。月光洒在沙滩上,湿沙依旧能显字。我蹲下身,用手指写下:
>“爸,我听见你了。
>妈,我也听见你了。
>这世界还有很多听不见的人,
>但我会继续说,
>直到他们也能开口。”
字迹刚成,海面便泛起幽蓝的光。涟漪扩散,拼出一行回应:
>**“孩子,你不是一个人在说。
>你只是第一个,
>把沉默翻译成光的人。”**
我仰头望天,星辰如雨。远处,苏砚站在礁石上,手中的玻璃罐高高举起,那颗光心冲天而起,化作一道流星,划破夜幕。
我知道,那不是结束。
渊语仍在生长,心脉仍在延伸,而《心礁录》的第一页,永远写着:“未完待续”。
人类终于学会了一件事:不必完美,不必正确,不必被理解。只要敢说,就有回声。
而回声,终将唤醒沉睡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