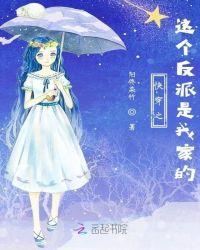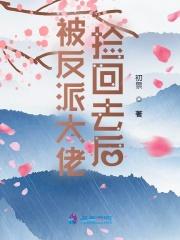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我在西游做神仙 > 第六十四章 天蚕身死(第2页)
第六十四章 天蚕身死(第2页)
阿禾睁开眼,泪水滑落。
她终于明白,所谓“西游”,并非奔赴某个圣地,而是唤醒沉睡的灵魂。她所做的,不过是轻轻推了一下那扇沉重的门,而后千千万万人便自己走了出来。
她走出石塔,迎着风雪,缓缓盘膝坐下。苏怜默默递上梅枝,她接过,轻轻插入雪中。
奇迹发生了。
那枯枝竟开始生长,抽芽、展叶、开花,短短片刻,便化作一株矮小梅树,枝头十二朵梅花同时绽放,每一片花瓣都透出柔和光芒,宛如星辰落地。
“这是……?”苏怜震惊。
“薪种不再藏于血脉,也不再依赖秘法。”阿禾轻声道,“它现在存在于信念之中。只要有人愿意为他人取暖,哪怕只是烧开一壶水,递出一碗热汤,薪种就会在他心中发芽。”
她抬手一指,一朵梅花飘起,飞向天空,化作流星划破长夜。
与此同时,万里之外,东海渔村的一位寡妇正为病儿熬药。灶膛火苗微弱,她低声祈祷:“若有神明听见,请赐一点热。”话音刚落,窗外流星掠过,一道金光落入灶中,火焰轰然腾起,久违的暖意弥漫全屋。
同一时刻,北疆戍卒在哨岗搓手呵气,忽然感觉胸口发热。他低头一看,贴身收藏的那张画着简笔梅的纸片,竟泛起温光,驱散了刺骨寒风。
更远的地方,沙漠深处,一支迷途商旅濒临绝境。领队老人仰望星空,喃喃道:“若阿禾还在走,就请给我们一点指引。”话音未落,沙丘顶端浮现一行发光脚印,一路向西,延伸至绿洲边缘。
十二朵梅花,逐一升空,化作十二道流光,射向四方。
从此,天下各地陆续出现奇异景象:
深山古寺的铜钟无故自鸣;
废弃祠堂的香炉莫名复燃;
甚至连囚牢铁栏之间,也有囚犯用指甲刮擦墙壁,刻下一朵小小的梅。
人们开始相信,火不只是工具,更是意志的延续。他们不再等待救世主,而是彼此扶持,自发组织“暖社”、“共炊堂”、“灯行会”。就连曾经镇压薪行会的官吏,也有不少人暗中资助这些民间组织,只因亲眼见过母亲抱着发烧的孩子奔向公共暖屋时那般急切的眼神。
三年后,大旱席卷中原,赤地千里,井泉枯竭。朝廷束手无策,豪族囤粮自保。就在百姓即将暴乱之际,一群布衣男女自西而来,肩扛陶瓮,手执梅枝,在干裂的大地上行走七日,最终停在一株枯死的老槐树下。
为首女子取出一枚透明果实,埋入土中,然后点燃脚下枯草。
火焰升起的那一刻,大地震颤,地下水脉复苏,清泉自根部涌出,迅速形成一口活井。更奇的是,那老槐竟在三日内返青,枝头开出罕见的红梅。
村民跪拜,称其神迹。
女子摇头:“非我之力,乃众人心火所聚。你们若不信,可试着一起点火,一起祈愿。”
于是百人围圈,每人点燃一小堆柴,齐声念诵《薪火谣》。不到半个时辰,方圆十里内接连冒出十七眼温泉,稻田重获生机。
此事传入京师,皇帝震怒又惶恐,召集群臣议策。有大臣主张剿灭“妖党”,以防民心失控;亦有谏官直言:“彼虽无名号,却有仁政之实。今百姓称其‘活菩萨’,不如招抚封赏,借其德望安定天下。”
皇帝犹豫良久,终派钦差携诏书西行,欲封阿禾为“护国真人”,赐庙宇千间,许其开宗立派。
使者寻至昆仑道口,只见一座茅屋孤悬崖边,屋前晒着几件补丁麻衣,檐下挂着一盏残破灯笼,灯罩绘梅,芯火将尽。
屋内无人,唯桌上留信一封:
>君以庙宇许我,我以人间报之。
>神若需香火供养,便不再是神。
>我非真人,亦非菩萨,不过一介点火人。
>若君真愿济世,请开仓廪,减赋税,允百姓相扶自救。
>如此,则处处皆庙,人人皆神。
使者读罢,久久不能言。回朝后如实禀报,皇帝默然良久,竟破例下旨:废除“禁私聚火令”,允许民间设立共暖之所,并拨款修缮道路,便利灾民迁徙。
消息传出,举国震动。有人欢呼,有人冷笑,更多人只是默默收拾行囊,加入西行队伍。
十年光阴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