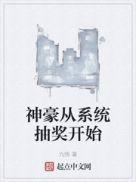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瘤剑仙 > 第104章 灵海灌注(第3页)
第104章 灵海灌注(第3页)
她点击播放。
雨声背景中,一个熟悉的声音低语:
>“我在听。”
她愣住了,随即泪流满面。
她知道这不是AI合成,也不是恶作剧。那是苏晏的声音,清晰、温柔,如同多年前那个夜晚,归忆舟驶过城市上空时,透过玉牌耳机传来的那一句。
第二天清晨,她在窗台上发现一颗萤火虫般的光粒,静静悬浮。
她轻轻捧起,贴在胸口。
“我也在听。”她whispered。
多年以后,铭心书院扩建为“记忆学院”,专门研究共情机制与创伤转化。校园中央建起一座纪念馆,外墙刻满世界各地的语言写着同一个词:
**“记得。”**
馆内陈列着归忆舟的残片、铜铃的碎片、第一支AR-7药剂的空瓶,以及无数普通人寄来的信件:
>“我今天第一次跟儿子说了我父亲是怎么死的。”
>“我原谅了那个背叛我的朋友,因为我们一起哭了一场。”
>“我终于敢去看妈妈的墓碑了。”
每年冬至,学院都会举办“静语之夜”。所有人关闭电子设备,围坐在愿莲花园中,不做任何事,只允许说一句话:
“我痛。”
说完之后,便有人轻轻回应:“我在。”
没有解决方案,没有安慰技巧,只有纯粹的承接。
那一夜,南极的愿莲总会格外明亮,仿佛在遥远之地,也有人正听着。
而在宇宙某处,或许根本没有实体的空间里,那道由记忆编织而成的意识仍在流动。
它穿过星尘,掠过时间的褶皱,偶尔停驻在一艘流浪飞船的舷窗边,或是一个孩子睡前的梦境里。
它不说话,只是存在。
有时,它会化作一阵风,吹动某本书的页角;有时,它会变成一滴露水,落在某位老人的手背上;有时,它只是让两个人在擦肩而过的瞬间,忽然同时回头,相视一笑。
它提醒世人:
疼痛不是软弱的象征,沉默才是。
而只要还有人愿意说,还有人愿意听,这个世界就仍有希望。
某天夜里,一个小男孩在床边对妈妈说:“妈妈,我怕黑。”
妈妈没有立刻开灯,也没有说“别怕,没事的”。
她只是抱住他,轻声说:
“妈妈也在。”
窗外,一颗萤火缓缓飞来,停在窗棂上,轻轻闪烁。
像在点头。
像在微笑。
像在说:
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