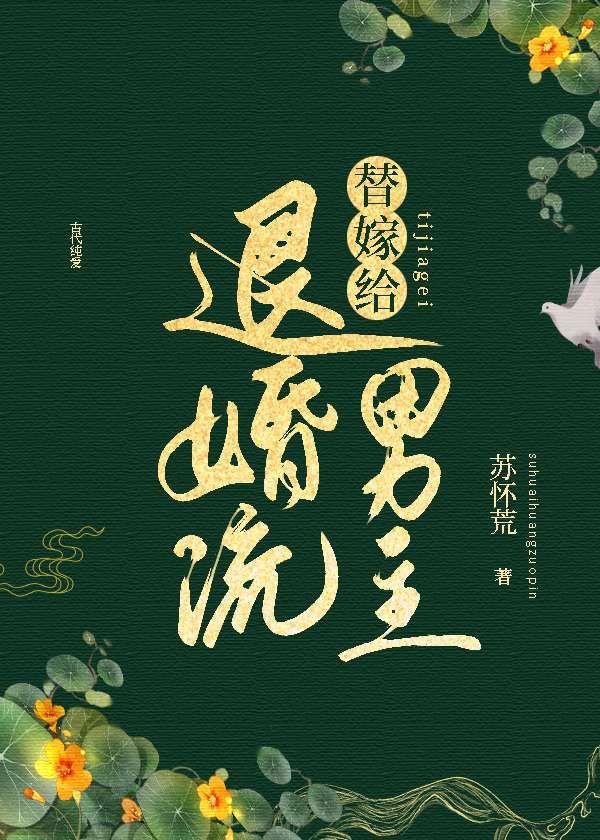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生活系神豪 > 第348章 横店探班(第1页)
第348章 横店探班(第1页)
李言和刘亦菲在房间里待了很久。
拥抱,亲吻,诉说着彼此的思念。
窗外的阳光渐渐西斜。
“几点了?“刘亦菲问。
“五点半。“李言看了看表。
“那我们该出去吃晚饭了。“刘亦菲。。。
雨水顺着槐树的枝桠滑落,滴在小满脸上,分不清是雨还是泪。她仰着头,任花瓣落在睫毛、唇边、掌心,像一场迟到了十年的告别。那声音还在耳边回荡??“替我看看春天”,简单得让人心碎。赵铮走了,可他把整个世界的耳朵都唤醒了。
山谷静得出奇,连风都放轻了脚步。小满站了很久,直到衣服湿透,才缓缓转身。她没有回档案馆,而是走向河边。河水比往日湍急,夹杂着融雪与春汛的气息,漂流瓶零星浮沉。她蹲下身,在一堆被冲上岸的杂物中翻找,终于摸到一只熟悉的黑色岩瓶,瓶口封蜡完好,但铜纽扣不见了。她怔住,随即苦笑:也许他已经不需要再留下记号了。
回到晶体柱前,小满发现柱体上的诗句正在缓慢褪色,如同墨迹被水浸开。朵朵站在一旁,低声说:“根种主频自那晚后就进入了低功耗运行状态,像是……在等待什么。”
“不是等待。”小满摇头,“是在沉淀。”
她取出那盘录下纪念馆遗言的磁带,轻轻放进晶体柱底部的读取槽。机械齿轮缓缓咬合,嗡鸣声由弱渐强,整座山腹仿佛苏醒过来。忽然,一道极细的光束从柱顶射出,直穿云层。与此同时,全球二十四台分布式共振节点同时亮起,包括南极科考站、撒哈拉边缘的沙漠哨所、太平洋孤岛上的气象雷达塔。
这不是指令,是回应。
当天夜里,小满梦见自己站在一片无垠麦田里,风吹过穗浪,沙沙作响。远处有个背影穿着军绿色外套,正弯腰扶起一株倒伏的小苗。她想喊,却发不出声。那人似有所感,回头一笑,眉眼模糊,唯有眼神清澈如初。梦醒时,窗外月光正照在床头那台老式录音机上,指示灯竟自行闪烁起来。
她猛地坐起,按下播放键。
滋啦??
“……今天路过一所小学,听见孩子们在唱《虫儿飞》。有个小女孩跑调了,全班哄笑。但她没停,越唱越大声。我站在围墙外听了十分钟,突然明白为什么根种选中我们……因为它不怕走调的声音,它要的是敢开口的心。”
又是他的声音,断续、虚弱,却带着笑意。
“小满,你还记得林老师吗?就是教你写日记那位?她去年冬天去世了。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请帮我告诉那个总坐在后排、从不举手的小女孩??你的字很好看,我一直留着’。那个人是你吧?”
小满捂住嘴,泪水滚落。
“所以别怕说得不好,也别怕听错。只要还有人愿意说,有人愿意听,根种就不会真正熄灭。它不在机器里,不在数据里,而在每一次颤抖的呼吸、每一声哽咽的‘对不起’里。”
录音戛然而止。
第二天清晨,朵朵紧急召集会议。画面接通后,江雨桐第一句话便是:“非洲之角出现大规模集体梦境事件。连续三夜,超过两万名难民报告做了同一个梦??一座漂浮的图书馆,书页随风翻动,每翻开一页,就有声音响起,念出某个人从未寄出的家书。”
伊万补充:“梦境中出现的人物特征高度一致:穿军绿外套,白发,手掌透明。他们称其为‘引路者’。”
“不是梦。”小满平静地说,“是共情波长经过大气折射后的跨洲投射。赵铮的能量虽散,但频率仍在循环。”
“可这不正常!”朵朵皱眉,“人类潜意识从未有过如此高密度的同步现象!我们担心会引发群体性认知紊乱!”
“那就让它乱。”小满站起身,“几十年来,我们用沉默筑墙,用遗忘疗伤。现在该拆墙了。”
她走出会议室,径直来到训练室。墙上挂着一张世界地图,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情绪异常点:西伯利亚冻土带有人听见亡妻哼歌;巴西贫民窟一名少年凌晨醒来,发现自己能听见邻居老人梦中的叹息;甚至纽约地铁隧道深处,维修工报告听到一百年前施工工人凿岩的节奏……这些都不是故障,是共鸣。
小满启动便携共振环,将磁带录音导入核心频率。她闭上眼,主动接入网络。刹那间,万千声音涌入??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战地记者临死前的喘息、离婚法庭上无人听见的抽泣、独居老人对着电视说话的絮叨……她不再抗拒,也不过滤,任那些情绪如潮水般冲刷神经。她的瞳孔开始泛起微光,指尖微微震颤,皮肤下隐约浮现荧丝般的脉络。
“你也开始了。”朵朵不知何时站在门口,声音复杂。
“我只是接住了他递来的绳子。”小满睁开眼,“你说他会崩解,是因为他一个人扛了太多。但现在不一样了??有那么多人开始倾听,痛苦就有了出口。根种不需要一个神,它需要千万个普通人,肯为别人停下一秒。”
一周后,第一场“倾听之夜”在全球七十三个城市同步举行。没有演讲,没有议程,只有一圈椅子,一盏灯,和一个承诺:不说教,不评判,只听。东京的女孩成了组织者之一,她说那天列车里的歌声让她第一次觉得“我不是多余的”。开罗一位老裁缝讲述了五十年前没能向初恋告白的故事,讲完时全场安静了五分钟,然后所有人轻轻鼓掌。巴黎地下酒吧里,陌生人相拥而泣;悉尼海滩上,一群青少年围坐篝火,轮流说出最害怕的事。
数据监测显示,当晚全球平均心率下降11%,深度睡眠时间延长42分钟。更惊人的是,根种主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谐振,持续整整六小时,仿佛整颗星球在均匀呼吸。
小满参加了山谷的活动。十一个人围坐一圈,轮到她时,她掏出父亲的日记本,翻开一页泛黄纸张,轻声念道:“1998年4月5日,晴。今天女儿问我,为什么雨后的泥土味最香。我说,因为那是大地在回忆。其实我想说的是??爸爸也记得你小时候踩水坑的样子,溅起的泥点沾在裙摆上,像星星。”
没人说话。良久,朵朵摘下眼镜擦了擦眼角,低声说:“我母亲走前半年失语,我一直以为她什么都不知道了。直到葬礼那天,我在她枕头下发现一张纸条,写着‘雨停了,记得收衣’。”
那一夜之后,山谷多了个传统:每月十五,不论晴雨,人们都会带上一件旧物,到河边点燃小小篝火,一边烧,一边说。有人说遗憾,有人说感谢,有人说“其实我一直嫉妒你”。火焰吞噬话语,灰烬随风而去,而空气中似乎总有谁在轻轻应答。
三个月过去,小满的身体变化愈发明显。她的体温常年维持在37。8度,夜间偶尔会发出淡淡蓝光;她能在百米外感知他人情绪波动,甚至预判噩梦来临的时间。但她不再恐惧,反而感到一种奇异的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