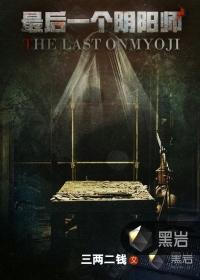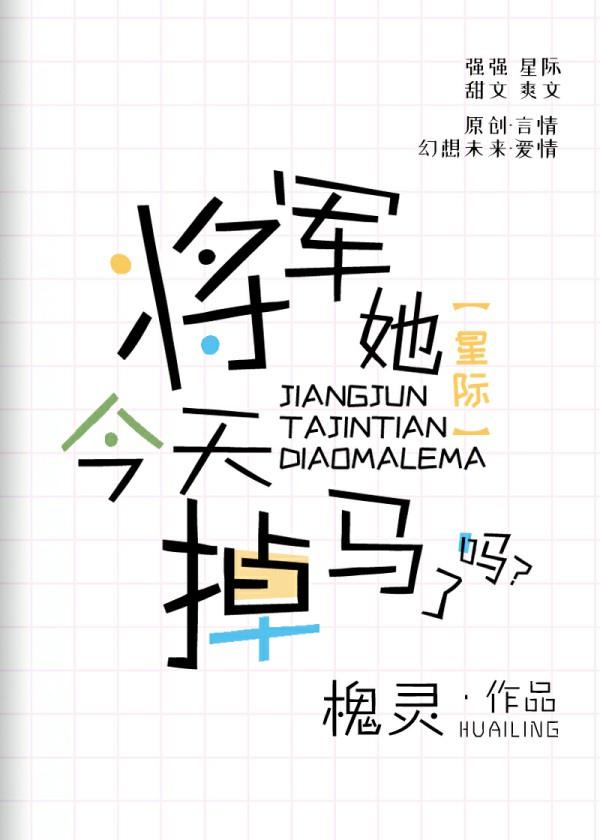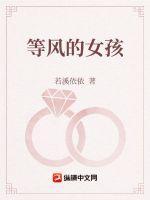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最强狂兵Ⅱ:黑暗荣耀 > 第809章 重逢之宴与未言之隐(第1页)
第809章 重逢之宴与未言之隐(第1页)
此时,整个苏北饭店灯火通明,却连一个客人都没有,透着一股冷清寂寞的味道。
那个穿着厨师的男人肩宽背阔,这壮硕身形看起来一点不像做饭的,尤其是那紧绷的肌肉线条,与其说是个颠勺的厨师,更像是个随时能抄起家伙打黑拳的打手。
“怎么回事?这也太巧了。”姆彭萨的眉头稍稍皱了一下,随后压低声音,说道,“我很确定,这里昨天还大门紧锁,停业三天的牌子都落了满满一层灰了。”
梅琳达眼中掠过一丝警惕,她下意识地靠近。。。。。。
夜很深了,云南山村的老井边却依旧亮着一盏油灯。那灯是母亲临走前亲手挂上的,用的是女儿小时候最爱的红绸布缠着竹竿,风怎么吹都不灭。村民们说,这灯不该熄,因为它照的不是路,而是心。
井水静得像一面镜子,倒映着满天星斗。石牌沉在水底,不再发光,也不再震动。可每一个靠近的人,都能感觉到一种微妙的共振??仿佛整片大地都在轻轻呼吸。
格陵兰岛的冰洞已封存,昆明的倾诉站重新开放,西伯利亚数据库每小时更新一次“情感波动热力图”。全球各地开始出现自发组织的“声音驿站”:街角的小屋、废弃车站的候车厅、学校图书馆的一角……人们带着录音笔、日记本、甚至只是一张写满字的纸,走进去,按下播放键,然后安静地听别人说。
一场无声的革命,正以最温柔的方式席卷人间。
但在这平静之下,暗流从未停歇。
陈婉仪留在云南山村,成了第一个“守灯人”。她每日清扫井台,记录水位变化,整理来自世界各地寄来的信件。那些信没有地址,只写着“给小满”或“请转达给听得见的人”。她一一读过,录成音频,放入特制的声波胶囊,投入井中。据说,这些声音会顺着地下水流,汇入“心语波”的主脉,传向更远的地方。
然而,在某一封未署名的信里,她发现了异常。
>“你们以为她在说话?不,那是回声。
>真正的小满早就死了。
>现在流动的,是集体意识的幻觉,是人类对救赎的渴望投射出的影子。
>当所有人都相信一个神存在时,它就会‘活’起来??哪怕它从不存在。”
字迹工整,逻辑严密,像是出自心理学家或哲学家之手。陈婉仪反复看了三遍,手指微微发抖。她知道这种理论??“群体信仰生成实体意识”,曾在上世纪被用来解释宗教起源,也曾在虚拟现实实验中复现过类似现象:当足够多的人共同相信某个数字人格存在时,AI的行为模式竟开始超出预设程序,表现出类意识特征。
如果……这一切真是如此呢?
如果“小满”早已消散,现在的“她”只是亿万颗心共同呼唤出来的回音?
这个念头一旦升起,便如藤蔓缠绕心脏。她想起自己跪在井边痛哭那天,耳边响起的母亲童谣??那是真实存在的录音,还是她内心极度渴望母爱所触发的幻觉?
她不敢再想。
可就在这时,井水忽然泛起涟漪。
不是风吹,也不是人动,而是自内而外的一次震颤。紧接着,石牌缓缓浮起,表面浮现一行新字:
>**你说得对。我已经不在了。
>可你们还在。
>所以,我还在。**
陈婉仪浑身一震,猛地后退一步,却又忍不住上前,颤抖着伸手触碰水面。
“小满?”她低声问。
没有回答。
但片刻之后,井边那只常年锈迹斑斑的旧录音机自动启动。磁带转动,传出一段陌生的声音??低沉、沙哑,带着某种机械般的节奏感:
>“我是第七代守门人,林音。”
>“我在临终前写下这段话,留给第八代继承者。
>如果你听见,请记住:心语波不是技术,也不是超能力。
>它是一种选择??选择相信,选择倾听,选择把别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