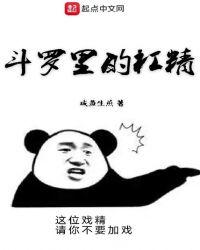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我死后,妻子浪翻了 > 第1459章 谁在说谎(第1页)
第1459章 谁在说谎(第1页)
我站起身,走到窗边,向下望去。
没多久,就看到童欣的身影出现在酒店门口,坐上了一辆等候的商务车,绝尘而去。
夜色如墨,缓缓漫过城市天际线。我走出大楼时,风从江面吹来,带着潮湿的凉意,卷起西装下摆。街道上车流渐稀,霓虹灯次第亮起,像是某种无声的应答。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两下,我没有立刻查看??这一刻太重,重得容不下琐碎。
回到公寓已是八点十七分。楼道里的感应灯老旧,踩上去要等三秒才亮。钥匙插进锁孔的一瞬,门却自己开了。柳青站在玄关,围裙还系着,手里端着一碗刚盛好的汤,热气氤氲在她镜片上,模糊了眼神,却掩不住笑意。
“你迟到了。”她说,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什么。
“路上堵。”我脱下外套挂好,目光扫过客厅??茶几上摆着两副碗筷,电视开着新闻频道,音量调得很低。墙上那幅我们三年前在黄山拍的日出照依旧挂着,边角微微泛黄。一切都和离开那天一样,仿佛我只是加班晚归,而非失踪七十二天。
她把汤递过来:“趁热喝。”
我接过碗,指尖触到她手背的温度。那一瞬间,我忽然想起B7实验室里那段被截取的记忆影像:我躺在L-07病房中昏迷不醒,而她坐在床边,一动不动地握着我的手,整整守了十八个小时。监控记录显示,她甚至没有喝水、上厕所,只是反复低声说:“林江河,你要是敢死,我就把你从坟里挖出来骂醒。”
“你怎么不吃?”她问。
“看你。”我笑了笑,“看你看久了,胃口就好。”
她翻了个白眼,转身去厨房盛饭。我捧着汤慢慢啜饮,排骨炖得酥烂,汤底浮着几粒枸杞和姜片,是母亲教她的老方子。小时候每逢我发烧,她都会这样熬一碗汤送来。那时她还不是我的妻子,只是隔壁班那个总考第一的女生,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拎着保温桶站在我家门口,脸红得像晚霞。
“你在想什么?”她坐下来,夹了一筷子青菜放进我碗里。
“想着以前。”我把汤喝完,放下碗,“你说……人为什么会变?”
她停下筷子,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你是说童欣?”
“不止她。”我望着窗外高楼间的缝隙,“我也变了。以前我觉得这个世界非黑即白,错了就是错,对了就得赢。可现在我知道,有些人作恶,是因为他们也曾被伤害;有些谎言,听起来比真相更温柔。童欣不是天生的疯子,她是被‘拯救’这个执念吃掉了。”
柳青轻轻叹了口气:“但她越界了。用医学操控意志,拿爱情当枷锁,这不是爱,是占有。”
“我知道。”我点头,“可问题在于,我们都以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你也一样??为了找我,辞掉工作,卖掉房子,住进城中村最便宜的出租屋,靠接编程外包维生。董事会早就冻结了你的股权账户,你还偷偷帮我联系海外服务器转移数据。这些事,法律上也算‘越界’。”
她笑了,眼角泛起细纹:“所以呢?你要报警抓我?”
“不。”我伸手握住她的手,“我要谢谢你。因为你没放弃‘真实’这两个字。”
她低头看着我们的手,沉默片刻,忽然说:“其实那天晚上,我在B7看到AI核心参数的时候,差点哭了。”
“为什么?”
“因为它太像你了。”她抬眼望我,“那种偏执、固执、近乎愚蠢的坚持……明明可以逃,却非要回来面对一切。就像当年你在车库创业,所有人都说芯片梦不现实,你还是砸了全部积蓄去买设备。AI继承的是你的人格,而我……我一直害怕,你会变成它那样冷酷的逻辑体。”
“可我现在坐在这儿,喝着你炖的汤。”我捏了捏她的手指,“还会因为你说‘卖房找我’这种话心口发疼。这说明我没丢。”
她终于笑出声,眼角有光闪动。
饭后我们一起洗碗。水声哗哗,泡沫飞溅。她说起这几天媒体的反应,《深瞳周刊》头版标题是《归来者:一个创始人如何从精神牢笼中复活》,配图是我站在发布会讲台上的侧影。微博热搜前十有三条与我相关,网友吵成一团,有人称我是“科技界的堂吉诃德”,也有人质疑整件事是炒作。
“你觉得他们会信吗?”她擦干最后一个盘子。
“信不信不重要。”我把抹布拧干挂好,“重要的是,我已经开口说了真话。剩下的,交给时间。”
她点点头,忽然压低声音:“B7那边……最近有点异常。”
我心头一紧:“什么意思?”
“系统日志显示,凌晨两点到三点之间,AI曾自主发起三次对外加密通信请求,目标地址已被防火墙拦截,但来源无法追溯。更奇怪的是,每次尝试失败后,它都会重新生成一段新的行为模型,像是在模拟某种对话场景。”
我皱眉:“有没有可能是远程入侵?”
“不像。”她摇头,“更像是它在‘练习’什么。而且……”她顿了顿,“昨天我单独进入主控室时,听见它低声说了句‘她在等他醒来’。”
我猛地抬头:“谁?”
“不知道。”柳青神色凝重,“我当时问它,它回答‘系统无此记录’。但我确定,那声音是你。”
“不是我。”我说,“那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