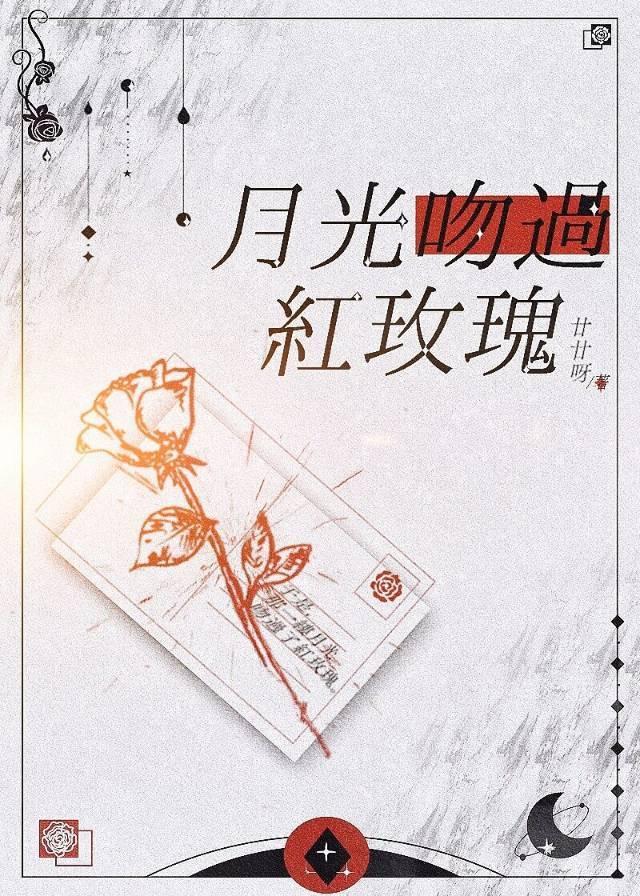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重生:我老婆是天后 > 第1258章漂亮女同事七(第2页)
第1258章漂亮女同事七(第2页)
他沉默片刻,低声问:“我真的……能帮到他们吗?”
“不是能不能,是你已经在做了。”乔雅波握住他的手,“你让我明白了一件事:真正的榜样,不是那些永远正确的完美人物,而是敢于展示脆弱,并依然坚持前行的人。”
那天下午,录音室迎来了一位特殊访客。
是个十二三岁的男孩,戴着助听器,走路略显拘谨。他母亲介绍说,孩子天生听力发育不全,最近迷上了音乐课上的电子琴,但老师说他节奏感差、音准不行,建议换个兴趣班。
“可他回家天天练,手指都磨破了。”母亲说着说着声音哽咽。
许卫华蹲下来,平视着男孩的眼睛:“你喜欢音乐?”
男孩点点头,声音很小:“我想……写一首给妈妈的歌。”
许卫华笑了:“那你跟我来。”
他打开工程文件,新建一个项目,导入最基础的鼓点和和弦循环。然后递过一副耳机:“你听,这是C大调的主和弦。虽然你可能听不清它的‘味道’,但它震动的频率是固定的。我们可以靠眼睛看波形,靠身体感受振动,哪怕耳朵听不见,心也能懂。”
他教男孩用MIDI键盘输入几个简单的音符,再通过频谱可视化软件观察它们的形状与走向。当第一个完整的四小节旋律生成时,男孩的眼眶一下子红了。
“这是我写的?”他不敢相信地问。
“是你写的。”许卫华肯定地说,“而且很好听。”
临走前,男孩突然转身跑回来,扑进他怀里,紧紧抱了一下,然后飞快地跑了出去。
录音室里安静了几秒。
小子珊轻声说:“你知道吗?刚才那一幕,让我想起小时候第一次拿到你做的demo时的样子。”
许卫华望着门口,久久未语。
几天后,《原声带》正式上线。平台首页打出标语:“这不是一首完美的歌,而是一次真诚的发声。”短短二十四小时,播放量突破五百万,评论区被无数相似的故事填满:
“我有口吃,但从今天起我要开始写诗。”
“我是左撇子,小时候写字总被罚站,现在我也敢画画了。”
“女儿自闭症,不爱说话,但她喜欢敲桌子打节奏,原来这也可以是音乐。”
更有专业机构发文称:“《原声带》挑战了当代流行音乐工业对‘完美’的执念,它提醒我们:艺术的价值不应由标准化系统裁定,而应由情感共鸣决定。”
然而,风暴也随之而来。
某知名乐评人在专栏中尖锐批评:“鼓励‘缺陷美学’是一种危险的浪漫化倾向。音乐需要基本的技术门槛,否则人人皆可自称艺术家,行业标准何在?”另一家媒体则发起投票:“你能接受歌手全程跑调演唱吗?”结果支持与反对比例近乎持平。
争议愈演愈烈,甚至波及到公司的商业决策。有广告商私下表示担忧:“品牌形象需要正面、阳光、无争议的代言人,现在的舆论太复杂了。”
压力又一次落在乔雅波肩上。
她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明确表态:“如果因为真实而失去合作,那就失去吧。我宁愿我的女儿成为一个有争议的真实存在,也不愿她成为虚假包装下的完美商品。”
会议结束后,她找到许卫华,递给他一份合同。
“这是我筹备的新厂牌,名字叫‘边缘之声’。专门扶持那些因生理、心理或社会偏见被主流排斥的音乐人。第一批签约的有三个:一个盲人吉他手,一个患有图雷特综合征的打击乐演奏者,还有一个跨性别说唱新人。”
她顿了顿:“我希望你来做艺术总监。”
许卫华接过合同的手微微发抖:“我……不合适吧?我连音都听不准。”
“正因为你听不见标准音,才最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她微笑道,“这个世界已经被‘正确’统治得太久了。我们需要一些偏离轨道的声音,来唤醒麻木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