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皮小说网>重生:我老婆是天后 > 第1272章制作版权二(第1页)
第1272章制作版权二(第1页)
“来看看你”
张友笑着合上手里这本名叫《归尘》的小说。
他也就看张艺不在,知道她去其他来这里生孩子的女人房间聊天,所以随意翻看一下。
“那你怎么也不叫工作人员叫我一声”
张艺脸。。。
夜色渐深,医院走廊的灯光昏黄而安静。姜伊人靠在病床边的椅子上,眼睛干涩发胀,却不敢闭上。儿子的小脸依旧泛着不正常的红晕,呼吸虽已平稳许多,但每一次轻微的抽动都让她心头一紧。监护仪上的数字跳动着,像是一道无形的倒计时,提醒她刚才那一幕有多凶险。
大子珊坐在另一侧,膝盖上摊着一本薄薄的医学手册??是她在医院书店临时买的《儿科常见急症处理指南》。她看得极认真,指尖轻轻划过纸页,时不时抬头看看弟弟的脸色和仪器数据。那神情不像个孩子,倒像是个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的主治医生。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姜伊人终于忍不住问,声音沙哑,“中耳炎、颅内感染、白细胞指数……你到底还懂多少?”
大子珊合上书,抬眼看向母亲:“我去年自考了美国红十字会的急救认证,也读了一些基础医学课程。弟弟体质弱,我不想哪天他出事,我只能干看着。”
姜伊人喉咙一堵,差点又落下泪来。
她忽然想起几个月前的一件事。那天家里请了个新来的育儿专家来做评估,说小儿子免疫力差,建议减少外出、加强营养调理。当时张先生正忙着谈一个影视项目,随口说了句“听你的”,就走了。她自己也在为一部新剧试妆,只淡淡回了一句:“知道了,回头让保姆注意。”后来那报告被夹在一堆合同里,不知丢去了哪里。
可现在想来,那场谈话后没几天,餐桌上就开始出现特制的高蛋白辅食,牛奶换成了低敏配方,连玩具都定期用紫外线消毒。她一直以为是保姆勤快,直到此刻才明白??那是大子珊在默默执行那份被所有人遗忘的专业建议。
“你……一直在照顾他?”她轻声问。
“我只是做了我能做的。”大子珊低头整理弟弟盖歪的被角,“他是我弟弟,我不帮他,谁帮他?”
一句话说得平平淡淡,却像刀子一样割开了姜伊人心底最深的愧疚。
她这一生,演过无数角色:清冷孤傲的女杀手、温柔贤惠的妻子、坚韧独立的职业女性……可在现实里,她却始终没能演好“母亲”这个身份。对儿子,她是宠爱有余而细心不足;对女儿,她是忽视多于理解,甚至常常把她的冷静当成冷漠,把她的早慧当作不合群。
而现在,这个被她误读了十年的女儿,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这个家。
凌晨三点,护士进来查房,确认病情稳定后笑着说:“小朋友挺幸运的,送来得及时,用药也对路,再观察两天就能出院了。”
走之前,她特意看了眼大子珊:“小姑娘真厉害,要不是你提前处理,后果真的不好说。”
门关上后,病房重归寂静。
姜伊人望着窗外漆黑的天空,忽然开口:“明天银行开门我就陪你去。不只是保险,你想成立的那个基金,妈也支持你。”
大子珊微微一怔,随即摇头:“妈,不用勉强。我知道这事不小,得走流程、找机构、做审计……你现在最该做的是休息。”
“我不是勉强。”姜伊人转过头,目光坚定,“我是第一次真正听懂你在说什么。你说你要的不是钱,而是改变点什么。这比拿奖金更难,也更重要。所以这次,别想一个人扛。”
大子珊眼眶微热,低下头,手指攥紧了衣角。
她从不曾奢望父母能懂她。从小到大,她的思维跳跃太快,表达方式太直接,常让人觉得疏离甚至压迫。老师说她“情商偏低”,亲戚议论她“不像女孩子”,连父亲虽然欣赏她的能力,也总带着一丝警惕地提醒:“别太精明,容易伤人。”
可今晚,在这间弥漫着药水味的病房里,母亲第一次没有否定她,没有用“你还小”来搪塞她,而是认真地说:“我支持你。”
那一刻,她感觉心里某块常年冰封的地方,悄然裂开了一条缝。
第二天清晨,阳光透过百叶窗洒进病房。孩子退烧了,睁着湿漉漉的大眼睛喊“姐姐”。大子珊蹲在床边给他喂粥,动作轻柔得不像话。姜伊人站在门口看着,鼻子一阵阵发酸。
九点整,母女俩离开医院前往市中心的私人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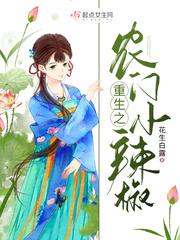

![[快穿]让反派后继有人吧!](/img/7543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