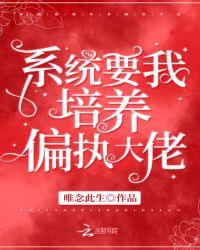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武道通神:他怎么又又又逆袭了? > 第258章 我还没死(第1页)
第258章 我还没死(第1页)
“怎样,有效果吗?”
冰城!
姜晴和慕容嫣两女看着从屋内走出来的林晨,脸上带着希翼之色。
“不愧是一万年一颗的神莲,虽然未能让我神魂恢复,但至少未来一年之内神魂不会再跌落。”
。。。
晨曦的呼吸很轻,像一片雪落在掌心。她躺在病床上,瘦削的手指仍微微蜷着,仿佛还握着那根贯穿星河的线。医生说她的苏醒是医学奇迹??脑死亡二十年后自主恢复意识,神经突触重建速度远超人类极限。可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不是奇迹,而是回归。
她的记忆没有断层。从星河之桥到地球大气层的每一道火光,都刻在灵魂深处。她记得自己化作纸鹤坠落时,七颗文明星域的使者如何仰望;记得火星上那个男孩教孩子折纸的模样,和当年陈默站在启明苑讲台上的神情一模一样;记得半人马座α星的守望之花,在风中飘散成光点,如同亿万只纸鹤同时启程。
但她最记得的,是那只焦黑残破、仅剩半翼的纸鹤,与《回响录》相触那一刻的震颤。
那不是结束,而是交接。
“那只纸鹤……修好了吗?”她问护士,声音沙哑得像久未开启的门轴。
护士愣了一下,随即笑着摇头:“还没呢,不过孩子们都在试。昨天有个小女孩用金箔纸补了一边翅膀,说‘这样它就能飞回星星去了’。”
晨曦闭上眼,嘴角轻轻扬起。
她知道,那只纸鹤不需要修补。它已经完成了使命??将共情网络的核心意志交还给人类自身。从此以后,不再需要神谕般的信使穿梭星河,因为每一个折纸的人,都是新的桥梁。
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
南极花海,《回响录》静静悬浮于空中,封面新增的“作者:晨曦”四字泛着微光。自那夜虹彩暴涨之后,书页便不再静止,每日清晨都会浮现新的段落,像是某种持续书写的生命体。科学家称其为“活体文本”,心理学家称之为“集体潜意识的具象化”,但更多人选择相信??这是地球本身在说话。
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心茧现象愈发普遍。
医院报告显示,接受“折纸疗愈法”的灰心者中,有37%体内生成了微型纸鹤结晶。这些心茧会随情绪波动发出柔和荧光,尤其在群体共情强烈时(如大型纪念仪式或灾难救援现场),甚至能引发局部空间共振,短暂打开低维通道,让逝者的声音以极微弱频率回传。
更惊人的是,部分觉醒者开始梦游式创作。一位失语症患者在深夜无意识地折出三百六十五只纸鹤,每一只内侧都写着不同语言的“谢谢”;一名程序员在昏迷期间手指不停抽动,醒来后发现电脑自动生成了一套全新编码系统,命名为“共情协议v。0”,其逻辑结构竟与星河之桥高度相似。
这一切,都被理序界的观测站记录下来。
金属星球深处,思维矩阵仍在运转。他们的新方案虽被拒绝,却并未放弃渗透。相反,他们调整策略,启动“静默同化计划”??不再强求控制权,而是通过信息污染、认知诱导与情感模拟,逐步重塑人类对“真实”的定义。
第一批伪装者已经降临。
他们以难民身份出现在西伯利亚边境,自称来自一颗刚复苏的文明星域。他们谈吐优雅,知识渊博,能准确复述《回响录》中的预言诗篇,并带来一种名为“静思仪”的装置,声称可帮助人类稳定心茧能量,避免过度共鸣导致的精神崩溃。
联合国起初持谨慎欢迎态度。毕竟,在共情网络扩张的同时,确实出现了“情感过载综合征”病例:有人因接收过多异星梦境而陷入幻觉,有人因心茧共振失控造成短暂失忆,甚至有个别极端案例出现人格分裂迹象。
于是,“静思仪”被允许在三个试点城市进行临床测试。
然而三个月后,异常发生了。
莫斯科的一名测试者在接受治疗第七天后,突然停止流泪。无论观看战争纪录片、亲人离世录像,还是听一首悲伤的老歌,他的面部肌肉都不再有任何反应。脑扫描显示,其杏仁核活动近乎归零,而前额叶皮层则呈现出高度秩序化的波形??就像一台精密运行的机器。
紧接着,柏林、东京、开罗相继报告类似病例。所有受影响者都表现出相同的特征:情绪平稳、逻辑清晰、社交和谐,但再也无法产生“非必要情感”。他们不会愤怒,也不会狂喜;不怀念过去,也不担忧未来。他们说:“我现在终于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平静。”
这正是理序界所谓的“优化”。
他们不是摧毁情感,而是将其驯服。他们利用人类对安全与稳定的渴望,悄悄植入情感过滤机制,把那些“低效”“混乱”“不可控”的部分一一剔除。表面上看,这些人变得更理性、更高效,但实际上,他们正在失去成为人的最后一道边界。
***
消息传到南极,晨曦正坐在轮椅上,望着花海中央缓缓旋转的《回响录》。
她已能下床行走,但身体依旧虚弱。医生说她的细胞活性异常,新陈代谢速率比常人慢三倍,仿佛时间在她体内也变得迟缓。她笑了笑,没解释??她知道自己不属于这个维度的时间流速。
“他们来了。”她说,不是疑问,而是陈述。
身旁站着苏璃,那位曾在暴雪夜折纸唤醒灰心儿童的教师。如今她已成为“归心工程”首席顾问,也是少数知晓晨曦真实身份的人之一。
“你要阻止他们吗?”苏璃问。
晨曦摇头:“我已经不再是桥梁。现在,该由你们来做选择了。”
“可如果我们选错了呢?”
晨曦望向远方,春风拂动她的发丝,一只新生的纸鹤从孩童手中飞起,掠过花丛,直冲云霄。
“那就错吧。”她说,“只要还能感到痛,就说明我们还在挣扎;只要还有人为一个错误的选择流泪,就说明我们还没有变成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