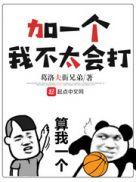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七零易孕娇娇女,馋哭绝嗣京少 > 第685章完美错过(第1页)
第685章完美错过(第1页)
一时间两人也顾不上做卫生了,打闹在了一起。
第二天家属院就通暖气了,屋里别提有多暖和了,家属院的人凑在一起讨论着。
现在政策是越来越好了,以后大伙的的日子越来越好过。
第二天一大早,江舒棠便早早起床,她刚把行李收拾好,就见顾政南在一旁眼巴巴问道:“真不用我跟着去?”
“孩子们盼这天盼多久了?再过阵子天气冷的不行了,爬山那是遭罪,下雪了,更没法去,你留在家里陪孩子吧,反正我过两天就回来了,也没什么大。。。。。。
晨光站在钟楼下,仰头望着那枚新铸的巨铃。夜风穿过山谷,吹动他额前碎发,也吹得铃舌轻晃,发出细微的嗡鸣。那一声声余音像是从地底升起的回响,又似来自遥远未来的召唤。他闭上眼,手指抚过盲文铭牌上的凸点,一字一句在心中默念:“听见的人,请回应。”
三日前,林溪的信再次抵达。信纸被雨水打湿过一角,字迹有些晕染,却依旧清晰可辨。
>南方的雨季来了,潮湿得连盲文都会发霉。
>但孩子们的手越来越稳,昨天有个小姑娘用“香味地图”独立完成了番茄炒蛋??她说那是太阳的味道。
>我教他们写“家”字的手语时,一个男孩突然问我:“老师,如果没人等你回去,家还在吗?”
>我愣了很久。
>最后我说:“家不是地方,是有人愿意为你留一盏灯的地方。”
>他哭了,我也哭了。
>晨光,我想你了。
>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要带着二十个学生一起来回声堂实习。他们中有聋哑人、盲童,还有一个因火灾毁容的女孩,她从不肯摘下口罩,却愿意为别人做饭。
>她说,食物不会嫌弃她的脸。
>所以,请把学院建得再大一点,好吗?
晨光将信折好,放进贴身衣袋。那里还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三年前矿难后,他在废墟里捡到的唯一物件:一张被烟熏黑边的合影。照片上是他与母亲,在草原上笑着牵马奔跑。如今边缘已被摩挲得发白,像一段不愿褪去的记忆。
他转身走回工棚,苏婉正伏案绘制课程表。油灯昏黄,映着她专注的侧脸。见晨光进来,她抬头一笑:“刚才巴图说地基打得不错,明天就能浇混凝土。”
晨光点头,在纸上写道:“让阿力负责震感测试。”
“明白。”苏婉记下,“他说现在能靠脚底感觉出地面是否平整,比尺子还准。”
晨光嘴角微扬。这世界总在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补偿那些失去感官的人。聋者听风知势,盲者触物辨温,残肢之人反而更能感知重心流转。这些曾被视为缺陷的能力,正在成为重建生活的基石。
翌日清晨,第一车水泥运抵。周振国带巡逻队协助卸货,玛依莎则领着几位老药师在药膳区试种新苗??一种耐阴湿的香草,据说可缓解焦虑情绪,适合精神障碍学员使用。
晨光独自登上钟楼,检查铃绳是否牢固。当他伸手拉动铜索时,整座山谷仿佛都为之震动。三声长鸣荡开,惊起一群飞鸟,远处放羊的孩子们停下脚步,齐刷刷转身面向钟楼方向,举起手打出“平安”手语。
就在这时,一辆军绿色吉普车卷着尘土驶入村口。
车上跳下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肩章已摘,但站姿仍带着军人特有的挺拔。他环顾四周,目光最终落在钟楼上那个沉默的身影。
“晨光?”他喊了一声,声音沙哑。
晨光身形一顿,缓缓转头。片刻后,他走下钟楼,一步步走向来人。
那人正是陈卫东,原矿务局安全科副科长,也是当年唯一坚持调查矿难真相的官员。事后被调离岗位,下放到边疆劳改农场十年。如今两鬓斑白,脸上刻满风霜。
“你还活着。”晨光终于开口,声音低沉。
陈卫东苦笑:“活下来了。可很多人没等到真相。”
两人对视良久。没有拥抱,也没有多余言语。但某种沉重的东西,在这一刻悄然落地。
当晚,众人围坐在灶房外的石坪上。篝火噼啪作响,映照着每一张脸。陈卫东讲述了这些年他如何辗转各地寻找幸存者档案,如何偷偷复制证据资料,又如何在边境小镇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提到了“回声堂”和一个叫晨光的男人。
“我以为你是死人名单里的名字。”他说,“没想到你不仅活着,还建了个……奇迹。”
“不是我。”晨光用手语配合口语慢慢说道,“是我们。”
林溪曾在日志里写过一句话:“一个人可以被摧毁,但一群人,能重新定义生存的意义。”此刻,这句话正真实地生长在这片土地上。
三天后,陈卫东决定留下。他主动请缨担任行政协调官,负责对接外界资源、申请办学资质、打通物流通道。“我不是教师,也不是医生,但我懂体制。”他说,“我可以帮你们绕开那些本不该存在的墙。”
与此同时,南方传来好消息:首批“香味地图”教学模块通过盲校评审,即将推广至全国五所试点学校。林溪的名字首次出现在教育部特殊教育简报中,被称为“感官替代烹饪法奠基人”。
而更令人振奋的是,那位毁容女孩??名叫小禾??在一次公开烹饪展示中摘下了口罩。她做的是一道极其简单的蒸蛋羹,却用了三种不同温度的水调配,只为让盲童同学能通过口感分辨出“冷、温、热”的差异。
她说:“我不能改变我的脸,但我能做出让人微笑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