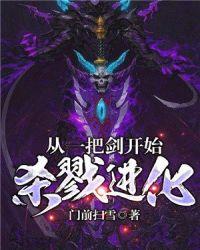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七零易孕娇娇女,馋哭绝嗣京少 > 第686章真的是四丫(第3页)
第686章真的是四丫(第3页)
“还能再利用。”他说。
于是,师生合力清理洞穴,在入口处铺设防滑通道,内部安装简易照明系统,并用回收材料搭建工作台。小禾提议在这里开设“荒野厨房”,教大家用有限食材制作营养餐。
第一顿饭,她做了野菜豆腐羹和烤薯饼。没有盐,就用晒干的柳叶灰代替;没有油,便提取坚果油脂。当热腾腾的食物端上来时,所有人都沉默了。
这不是一顿普通的饭。这是在绝境中开出的花。
三天后,道路抢通。救援车队带来补给,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消息:国家残联派出考察组,将在一个月内正式评估回声学院办学资质,若通过,将成为国内首家专为多重残障青年设立的职业教育示范基地。
消息传开那晚,整个学院沸腾了。
但他们没有庆祝太久。因为真正重要的事,才刚刚开始。
五月末,考察组如期而至。为首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官员,姓赵,曾任特殊教育司副司长。她全程沉默观察,不轻易提问,也不做笔记,只是认真地看着每一个细节:学生如何独立完成一道菜,教师如何用手语+盲文+震动提示协同授课,疗愈工坊里假肢适配的过程是否人性化……
最后一天,她单独约见晨光。
“你知道为什么上面迟迟不肯批这类学校吗?”她问。
晨光摇头。
“因为我们害怕。”她说,“怕投入资源却看不到成果,怕社会舆论说这是‘施舍’而不是‘教育’,怕一旦失败,就成了压垮政策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顿了顿,目光直视他:“但现在我看到了一样东西??你们不是在办学校,是在重建一种尊严。所以,我会签字。”
离开前,她在记忆墙上留下一句话:
>真正的公平,不是给人拐杖,
>而是让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如何站立。
六月初,批复文件正式下达。回声学院获得五年试点资格,首批经费拨付到位,同时还获批成立“感官创新研究中心”,可自主开展跨学科实验。
那天傍晚,夕阳洒满山谷。晨光独自登上钟楼,轻轻拉动铜索。
一声,两声,三声。
钟声荡开,惊起归鸟无数。远处田埂上,学生们正手拉着手往回走,笑声随风传来。小禾走在中间,脸上不再遮掩,阳光落在她疤痕交错的脸颊上,竟显得格外柔和。
林溪不知何时来到身后,轻轻靠在他肩上。
“你说,我们会一直这样下去吗?”她轻声问。
晨光转头看她,嘴角微扬。他拿出随身携带的日志本,在空白页写下:
>只要还有人愿意点亮灯火,
>这世间就不会再有真正的黑夜。
>而我们,
>会一直敲响这口钟,
>直到所有沉默的灵魂都听见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