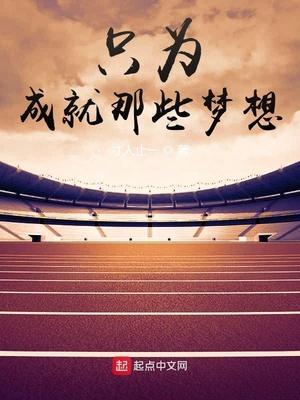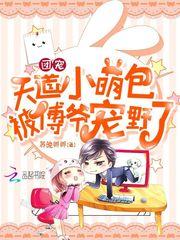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全家夺我军功,重生嫡女屠了满门 > 第740章 本事太大从死牢里捞人(第1页)
第740章 本事太大从死牢里捞人(第1页)
陈明月听到断头饭三个字,面色骤然惨白如纸。
她身子晃了晃,几乎要晕厥过去。
“能不能再晚一些?让我再跟爹娘多说几句话。”陈明月泪水氤氲眼眶,连忙从袖子里拿出一个银袋子递过去。
因为她知道,这顿饭一旦吃下,意味着行刑之期已不足十二个时辰。
那饭食里,按照规矩,掺了令人筋骨酸软的药物。
既是防止犯人临刑挣扎,也是绝了他们最后一丝逃跑或反抗的力气。
若吃了这断头饭,父母便连说话也要囫囵不清了。
狱卒坚决地推开。。。。。。
林昭雪写下名字的那一刻,窗外铜铃忽地一颤,余音拖得极长,仿佛被什么力量拽住,不肯散去。纸页上的墨迹未干,字迹却泛起微光,宛如活物般微微蠕动,竟自行延展成一行小字:**“我名既立,万声同鸣。”**
阿芜在观云台忽觉心口一震,似有千言万语自血脉深处涌上喉头。她低头看手,掌纹中竟浮现出细密金线,如音波流转,勾连成符。她猛然抬头,望向南疆方向??那一瞬,天地寂静,唯有风在耳畔低语:“第三次铃声,不在你手,而在你心。”
她闭目凝神,终于明白。
铃舌非器,而是契约之印;铃声非响,而是誓约之始。第一次唤醒记忆,第二次撕破谎言,第三次……是将沉默者的名字刻入律法、山河、人心,成为不可磨灭的根基。
她缓缓取出母亲留下的血玉印章,轻轻按在《女子授爵法》首卷之上。朱砂落纸,不只盖下官印,更似点燃一道火种。刹那间,京城九座回声井齐齐震动,井底共鸣石逐一亮起,映出百年前那些被焚毁的手稿、被抹去的签名、被踩进泥里的誓言。一道道虚影自井中升起,不是哭诉,不是控诉,而是站定,挺直脊梁,朗声报出自己的名字:
“沈兰!”
“苏婉儿!”
“林沈氏,沈云卿!”
“李红绡,北境戍边女卒!”
“赵三娘,黄河治水图主绘人!”
声音由井而起,穿街过巷,汇入宫墙,撞上金殿屋檐的铜铃。那铃本已被拆下封存,此刻竟无风自动,嗡鸣不绝。守库太监惊恐跪倒,只见原本锈蚀的铃身内壁,竟浮现出密密麻麻的小字??全是历代被宁心散侵蚀记忆的宫人亲笔所录的遗言,一笔一划,深入金属,如同用骨血刻就。
消息传至皇宫,皇帝正批阅边关奏折,闻讯起身,亲自前往藏铃阁。他亲手拂去尘灰,抚着铃身上的名字,久久不语。良久,他命人将此铃悬于太和殿最高檐角,并下旨:“此铃名为‘铭心’,自此日始,凡朝廷议政,必先听铃三声,以警天下??勿忘无声者。”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百日归名计划”进入高潮。一百零八州,每一处回声井旁都搭起铭名台,百姓携祖辈遗物而来。有老妇捧着半块焦黑的织机齿轮,说这是她祖母发明水力提花机时烧毁的原件;有盲眼老人摸着一块残碑,喃喃:“这是我娘写的诗,她说‘女子亦可题雁塔’,结果第二天就被沉塘了……”;更有远嫁西域的商旅后代,带来一封泛黄家书,上面写着:“吾女阿黛,通七国言语,曾为使节译通漠北诸部盟约,功归其兄。”
阿芜命人将这些一一录入《重修实录》,并设立“言脉史馆”,由春芽统领,专责考据、保存、传颂。每一份材料入库,皆需经三重验证:一是实物佐证,二是口述传承,三是音镂共鸣。唯有当回声井能唤出当事人的声音片段,才算真正“复活”。
然而,风暴并未平息。
第七日深夜,天听院外突现大火。火势自东厢燃起,直扑藏书楼。阿芜披衣而出,见数十黑影持刀纵火,口中高呼:“妖女惑众!焚书止乱!”她冷眼望去,认出其中几人竟是礼部暗卫,甚至有两名御前侍卫混迹其间。
“朝廷已下令取缔言种会?”她立于廊下,玄袍猎猎,声如寒冰。
一人狞笑:“昭明夫人?不过是个靠鬼神之术蛊惑圣心的贱婢!今日便叫你与你的‘亡魂’一同化灰!”
话音未落,春芽自屋顶跃下,手中短刃划破夜空,瞬息斩断三人兵刃。其余女官纷纷现身,手持录影铜匣,齐齐对准火场。阿芜抬手,水晶铃舌悬于指尖,轻轻一振。
铃声清越,穿透烈焰。
下一瞬,火光中浮现出无数身影??有被烧死的女匠临终前仍在绘制纺车图纸;有被活埋的医女在土下用指甲刻写药方;有被溺毙的才女,在水底默诵自己未完成的策论……她们的身影层层叠叠,环绕火场,口中齐诵《被遗忘者之誓》:
>“我们不曾消失,只是未曾被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