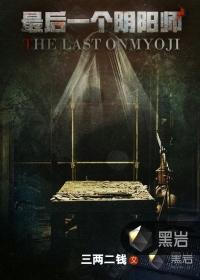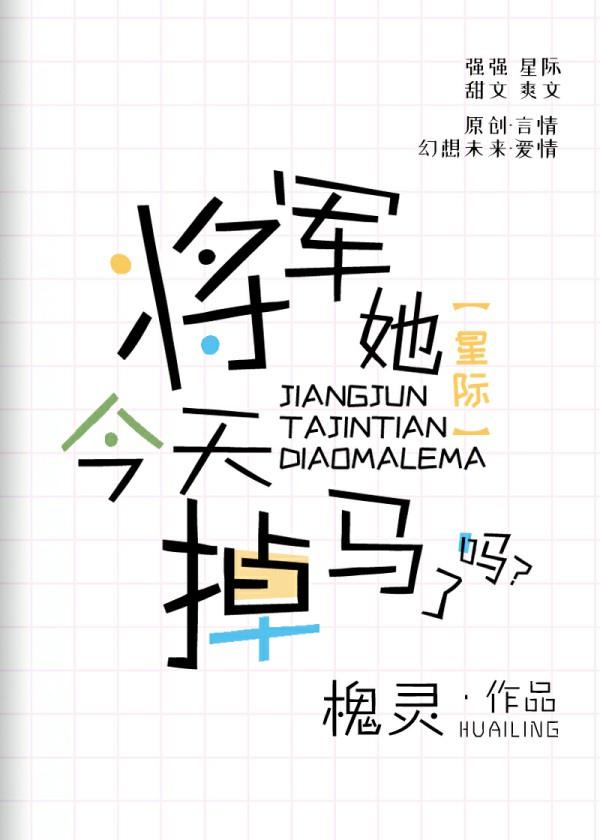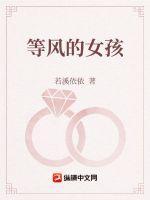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步步登阶 > 第628章 回到正轨(第2页)
第628章 回到正轨(第2页)
>标准符合度:98。7%。
>附注:请继续展示‘宽恕’的发生过程。”
“宽恕?”小卓玛读完译文,心头一震。
几天后,村子里发生了一件事。一名年轻牧民的儿子在放羊时误入雷区,虽未受伤,但受惊过度,整日蜷缩在帐篷里不言不语。孩子的父亲怒不可遏,提着鞭子冲到顿珠家门口,吼道:“都是你当年乱跑惹的祸!要是没有你那次逃跑,哪来的什么影叶林?哪来的鬼信号?我儿子现在吓成了傻子!”
顿珠没有辩解,只是静静地听着。直到那人骂完转身离去,他才走出门,跟了上去。
人们后来才知道,顿珠连续三天陪那位父亲守在儿子帐篷外。第一天,他讲自己小时候如何怕黑;第二天,他拿出城市高中课本,一页页读给男孩听;第三天夜里,男孩终于睁开眼,轻声说:“叔叔,你能抱抱我吗?”
顿珠抱住他,眼泪滚落。
第二天,那位父亲来到回声亭,在木牌上写下:
>“我对不起顿珠。我把自己的恐惧,变成了对别人的恨。现在我想学着把它变回来。”
当晚,共律系统再次捕捉到TZ-42α的波动。解码组还原出一段极短的信息:
>“观察到‘仇恨→理解’的转换路径。
>记录为案例#7429-A。
>进度更新:准备进入最终评估阶段。”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顺利跨越内心的深渊。
小卓玛收到一封来自日本的信。寄信人正是那位曾因杀人罪入狱、如今已重获自由的囚犯。他在信中写道:
>“我试着去见被害者家属,想当面道歉。可当我站在他们家门口,却怎么也不敢敲门。我怕看到他们眼里的恨,更怕听到他们说‘我们不原谅你’。
>可我又知道,如果不试,我就永远走不出监狱。”
小卓玛读完,久久不能言语。她想起十年前,自己也曾站在母亲坟前,一句话都说不出。有些话,比死亡还沉重。
她提笔回信:
>“你不必一定要得到原谅。
>你只需要让他们知道:那个夺走他们亲人的人,如今也会为一句‘对不起’颤抖。
>这就够了。”
信寄出两周后,对方发来一张照片:一扇老旧的木门前,地上放着一封信,旁边摆着一束白菊。没有署名,也没有回应。但他站在远处拍下了这一切,并附言:
>“我来了。我说了。我走了。
>我觉得自己……轻了一点。”
共律系统自动归档此事件为:
>**类型M-13“未完成的宽恕”**
>注释:非闭环情感表达亦具价值。
冬天渐深,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将在次年春季举行“全球倾听峰会”,邀请各国代表分享本土化实践。而作为发起地,羌塘草原被定为开幕式举办地。
筹备期间,争议也随之而来。有学者质疑:“这种基于情绪共鸣的社会实验,是否太过脆弱?一旦失去外部关注,会不会迅速瓦解?”
扎西在一次访谈中回答:“你以为它是靠项目维持的吗?不,它是靠人与人之间一次次真实的触碰撑起来的。就像火塘边的一句闲谈,教室里一次沉默的拥抱??这些事,从来不需要立项审批。”
话音未落,小卓玛匆匆赶来,脸色发白。
“出事了。”她说,“共律系统刚发出红色预警??TZ-42α信号进入倒计时模式,预计七十二小时后终止传输。最后一条解码信息是:‘最终测试即将开始,请准备好你们的答案。’”
所有人陷入沉默。
什么是“最终答案”?
三天内,世界各地的影叶节点纷纷做出回应。开罗的女孩们围坐一圈,轮流讲述自己遭受歧视的经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出现了上千个“匿名倾诉箱”;挪威的心理学家组织了一场“静默葬礼”,让人们为未曾说出口的爱与悔意哀悼。
而在羌塘,仁青提议举行一场“无言仪式”。
“我们已经说了太多。”他说,“现在,让我们学会用沉默去听。”
仪式定在雪夜。全村人聚集在回声亭周围,每人手持一支蜡烛,却不交谈,也不写字。只是站着,听着风穿过树林的声音,听着彼此呼吸的节奏,听着脚下积雪轻微的塌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