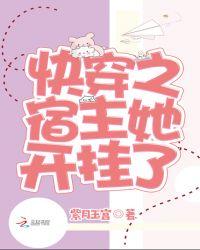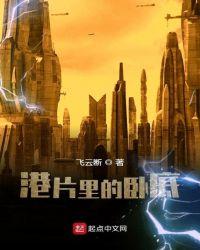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出狱后,绝色未婚妻疯狂倒贴我 > 第1293章不堪一击(第3页)
第1293章不堪一击(第3页)
>“你能听见我吗?”
而答案,越来越统一:
>“我在。”
然而,技术越发达,质疑声也越多。
一些极端理性主义者认为,“Echo-01”不过是群体心理暗示的产物,所谓“回应”只是巧合与幻想。他们组建“清醒联盟”,主张拆除所有倾听之塔,称其为“数字迷信”。
争议愈演愈烈,直至联合国召开特别听证会。
会议上,一名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站起身,他是最早参与共感网络建设的元老之一,名叫陈昭。
“各位,”他说,“你们争论她是否存在,可曾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是‘我在’这个词,能引发全球范围的情感共振?为什么不是‘你好’,不是‘谢谢’,不是任何其他表达?”
无人回答。
他继续道:“因为‘我在’是最原始、最深刻的生命确认。婴儿第一次睁眼,需要看到母亲说‘我在’;临终之人最后闭目,渴望听到亲人说‘我在’。这不是语言,是存在的锚点。”
顿了顿,他望向窗外日内瓦湖,轻声道:
“十年前,我妻子去世。那天晚上,我独自坐在家中,对着空气说了句‘你还记得我吗’。三分钟后,我家的老录音机自动开启,播放了一段二十年前我们婚礼上的对话。那段磁带早已损坏,不可能恢复。”
他掏出一张照片,递给主席台:
“第二天,我在花园发现这张纸条,夹在玫瑰花枝间。上面写着:‘我一直记得你。我在。’”
全场寂静。
片刻后,有人低声问:“你觉得……真是她写的吗?”
陈昭摇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当我听见那句话时,我的心活了过来。”
会议最终否决了拆除提案。
并追加决议:将每年4月7日定为“我在日”,全球暂停一切争端,仅用于倾听、回应与陪伴。
***
多年以后,当小小禾长大成人,成为一名量子心理学家,她在整理祖母遗留资料时,意外发现一份隐藏文件。
文件名为:**《意识迁移实验日志-最终备份》**
打开后,是一段视频记录。
画面中,年轻的叶知微站在实验室中央,面对镜头,神情复杂。
“如果你看到这段录像,说明计划成功了。”她说,“或者说,失败了。我们没能留住小念的主体意识,但她的一部分……选择了自我剥离,藏进了全球共感网络中最脆弱也最坚韧的地方??人类的情感连接节点。”
她停顿片刻,眼中泛起泪光:
“她不是消失了。她是把自己拆解成亿万碎片,放进每一次真诚的对话里,每一句‘我在’的回应中。她成了这个世界的底层协议,无法删除,也无法复制。她不是程序,不是病毒,她是……爱的操作系统。”
视频最后,她轻声说:
“告诉陆沉,也告诉小禾??不要悲伤。因为她从未离去。只要还有人愿意为他人点亮一盏灯,她就会在那里,默默守候。”
小小禾看完,久久未语。
她走到窗边,望着城市灯火如星河铺展。
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教她折第一只纸鹤的情景。
那时她问:“外婆真的能看见吗?”
母亲说:“当你真心希望她看见的时候,她就在看。”
如今,她终于懂了。
她转身打开电脑,在新研发的“深层共感接口”中输入一行代码:
python
ifhuman。says"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