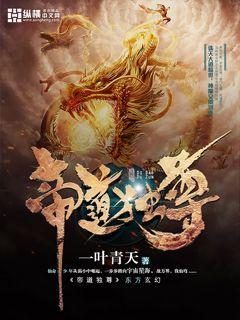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婚后失控 > 第741章 让自己累的感情不要(第1页)
第741章 让自己累的感情不要(第1页)
苏离和莫行远僵持着。
院长都出来了,看到他们站在一起,气氛也不太对,一时之间不知道该不该上前去打招呼。
“院长。”苏离主动喊了人。
院长冲她笑了笑,又看向了莫行远,又看了眼苏离。
“你们……认识?”院长觉得他俩,应该是认识的。
苏离微微一笑,“有过几面之缘。”
莫行远对她这个解释不满意,但他没有再火上浇油,点了一下头。
这个时候,莫行远的手已经拿开了。
“原来如此。你们这是……”院长看着他俩,“是有什么问。。。。。。
江临川在心理辅导室待了整整三个小时。他没有急着谈监护权的事,也没有翻阅张野的档案,而是坐在那张褪色的蓝色布沙发上,听少年断断续续地讲过去??关于父亲去世那天他正在打游戏,母亲最后一次回家是穿着湿透的外套站在门口说“我走了”,还有他在面馆里偷偷把眼泪滴进汤里的事。
“你不是不孝。”江临川轻声打断,“你是太想留住他们了。”
张野猛地抬头,眼眶通红:“可我连葬礼都没去!我爸火化那天,亲戚说我是累赘,把我关在门外……我只能蹲在墙角,听着里面念悼词。”
江临川沉默片刻,从包里取出一张照片,轻轻推到他面前。那是黄桷村小学的校门,阳光洒在爬满藤蔓的砖墙上,几个孩子正笑着跑过操场。
“这是我现在教书的地方。十年前,我也曾被人关在门外。”他说,“我母亲病逝时,家族会议决定把我送进福利院,理由是‘没人愿意养老师的孩子’。直到林晚老师翻山越岭找到我,她说:‘这个孩子有声音,不能让他沉默下去。’”
张野怔住。
“所以我今天来,不只是为了走程序。”江临川看着他,“我是来告诉你:你不必再等别人开门。你可以自己走进去,然后为下一个被拦在外头的人,留一扇门开着。”
那天傍晚,江临川带张野去了那家牛肉面馆。老板认出他,愣了一下:“小张?你还回来啊?”随即转身就进了厨房,“老规矩,加蛋!”
面条端上来时,热气氤氲中,张野的手微微发抖。他低头吃了一口,忽然停住,肩膀剧烈起伏。
“慢点吃。”江临川递上纸巾,“这碗面,是你爸的味道,也是你的。”
那一晚,张野第一次主动填写了《心理评估表》,并在“是否愿意接受长期心理支持”一栏,重重打了勾。临别前,他抱着书包站在宿舍楼下,终于问出口:“江老师,如果……我真的能去黄桷村,我能养一只猫吗?就像‘回声’那样的?”
江临川笑了:“只要你愿意照顾它,它就会陪你。”
回到黄桷村已是深夜。陈默还没睡,在窗边守着HJ-90的提示灯。听见车声便冲出门,浑身被雨打湿也不顾。
“怎么样?”他急切地问。
江临川摘下湿漉漉的风衣,眼神疲惫却亮着光:“他签了初步意向书。接下来,我们需要一份稳定的住所证明、两名担保人、以及至少六个月的心理观察记录。”他顿了顿,“还有,得让教育局相信,山谷学堂不是理想主义的空谈,而是一个可行的庇护系统。”
陈默咬唇:“那我们怎么做?”
“第一步,公开筹款与选址。”江临川摊开地图,“ideally是村里废弃的小学校舍,离主屋不远,又能独立运作。第二步,联系专业心理咨询师组成支援团队。第三步??”他看向陈默,“你要准备好,站出来说话。”
陈默心头一紧。
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再是匿名日记,不再是隔着屏幕的倾诉,而是要站在镜头前,说出那些他曾以为永远埋进心底的事:母亲早逝,父亲酗酒,童年蜷缩在灶台后背课文只为逃避拳脚,还有那个无数次想结束生命的雨夜。
“我怕……”他低声说,“怕说出来之后,大家会觉得我不是现在的我,而是可怜的我。”
江临川握住他的手:“但真实的你,才最值得被看见。不是作为受害者,而是作为一个活下来,并且选择去照亮别人的人。”
第二天清晨,陈默独自走进山间小路。他带着录音笔,沿着溪流走到半山腰的老槐树下??那是他小时候躲哭的地方。树皮上还刻着歪歪扭扭的“小默不怕”。
他按下录音键,声音微颤:“十年前,我在这里划破手腕,想着只要血流干了,就不会再疼。但我忘了,疼从来不在皮肤下面,而在没人听见我说话的时候。后来,有人听见了。现在,我想成为那个听见别人的人。”
这段录音,成了“山谷学堂”众筹视频的第一段素材。
视频发布第七天,点击量突破百万。一位知名公益博主转发并写道:“这不是慈善,是正义。我们亏欠这些孩子一场正式的道歉??为所有视而不见的年月。”
捐款如潮水般涌来。有打工的母亲捐五十元附言“我女儿也常做噩梦”;有退伍军人寄来三千元和一本旧军装照,写着“孩子需要安全感,我懂”;甚至一所重点中学的学生集体义卖文具,筹集两万元,信封上贴满了便利贴:“请给更多人一个家。”
资金初步到位,江临川开始着手修缮村东头那栋闲置多年的两层教学楼。屋顶漏雨,墙面霉斑遍布,地板松动得像老人脱落的牙。但阳光穿过破碎的玻璃窗洒进来时,依然明亮得令人动容。
施工第一天,陈默带着五名同学来做志愿者。他们清扫尘土,搬运木料,刷漆时笑闹着把彼此涂成花脸。李老师送来绿豆汤,站在门口感慨:“以前都说这屋子阴森,没人敢来。现在听,全是笑声。”
傍晚收工时,陈默发现楼梯拐角的墙上被人用粉笔写了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