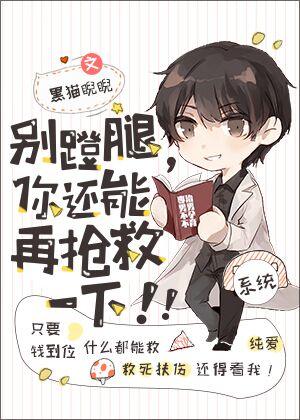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高武:陪练十年,一招出手天下知 > 第二百三十章 紫气东来(第1页)
第二百三十章 紫气东来(第1页)
海平面上,足有数十艘硕大的钢铁巨兽,劈波斩浪,伴着日落霞光,朝着岸边驶来。
与此同时,钢铁巨兽上飞出了数个如同鹰鸟的铁怪物,呼啸而来,很快便抵达了海岸上空,这些铁鸟并没有降落,而是悬停在空中,好。。。
沙……沙……沙……
那声音在清晨的薄雾中轻轻回荡,像是从地底深处浮上来的呼吸。苏念站在东海石碑前,指尖还残留着昨夜触碰符文时的微温。她没有回头,却知道晓尘已经走远??她的脚步总是轻得像一片落叶滑过水面,不留痕迹,却让整片湖心泛起涟漪。
天光渐亮,海风卷着咸腥的气息扑面而来,远处礁石上,几个少年正用竹帚清扫被潮水推上岸的垃圾。他们穿的是归尘学堂统一的灰布衣,袖口磨得发白,但动作整齐划一,仿佛不是在打扫,而是在书写某种无声的誓言。
苏念缓缓起身,沿着海岸线往南走去。这条路她十年前走过一次,那时她是来找林北的。如今林北早已不在,可他的影子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活在这片土地上。
走了约莫两个时辰,她抵达了一座小渔村。村子依山傍海,房屋错落有致,屋顶铺着青黑色瓦片,墙根下种满了忆尘草。正值初春,蓝花成片开放,在晨光中微微颤动,如同无数双睁开的眼睛。
村口立着一块木牌,上面刻着:“归尘?临海分堂”。
这里原是个废弃渔港,三年前因台风损毁严重,村民大多迁走。后来一群归尘志愿者自发前来重建,不为开发旅游,只为守住这片濒临消失的渔家记忆。他们在旧码头搭起学堂,请回年迈的老渔民教年轻人织网、识潮、辨星象;又把废弃渔船改造成流动图书馆,漂在近海,供岛民借阅书籍。
苏念走进学堂时,正逢早课。
孩子们围坐在院中一圈,每人手中握着一把小扫帚,闭目静坐。讲台上站着一位中年女子,是这里的负责人陈婉如,曾是省城重点中学的心理教师,五年前辞职加入归尘。
“今天我们不扫地。”她说,“我们先学‘听’。”
学生们睁开眼,露出疑惑神色。
“听什么?”一个男孩问。
“听扫帚的声音。”陈婉如轻声道,“不是耳朵听,是心听。你们知道吗?同一把扫帚,不同的人扫,声音是不一样的。急躁的人扫得重而乱,焦虑的人扫得快而碎,只有心里干净的人,才能扫出‘沙……沙……沙……’那种均匀的节奏。”
她顿了顿,目光落在门口的苏念身上,嘴角微扬:“就像现在,有人来了,可扫帚声没变??说明我们的心,还没乱。”
学生们顺着她的视线望来,纷纷起身行礼。苏念摆摆手,走到角落坐下。她看见墙上挂着一幅手绘地图,标注着全国三百所归尘学堂的位置,红线交织如脉络,竟与当年星图轨迹隐隐吻合。
课后,陈婉如带她参观学堂后院。那里有一棵老榕树,枝干盘曲如龙,树洞中嵌着一块铜牌,刻着“林北?守望者”五个字。
“每年清明,都有人从各地赶来,在这棵树下放一朵忆尘草。”陈婉如说,“去年冬天,有个盲童在这里住了半个月。他看不见花,却说能闻到‘光的味道’。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父亲曾是林北的学生,在矿难中去世。这孩子从小就没见过爸爸的照片,只记得他总穿着一双破胶鞋,天天去工地捡废品捐给学校。”
苏念沉默良久,忽然问道:“你们教孩子扫地,真的只是为了清洁吗?”
“当然不是。”陈婉如笑了,“扫地是最简单的仪式。它教会人低头,也教会人坚持。你看那些富人家的孩子,刚来时连扫帚都拿不稳,嫌脏、怕累、爱抱怨。可三个月后,他们能在暴雨里站三小时疏通排水沟,只为不让低年级同学踩水上学。这不是纪律训练,是灵魂的打磨。”
她指向教室窗外:“你知道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吗?是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女孩。她三年不说一句话,直到有一天,她看见一只受伤的海鸟躺在滩涂上,浑身沾满油污。她什么也没说,默默拿来扫帚和清水,一点一点帮它清理羽毛。整整两天,她不吃不睡,就守在那里。最后鸟飞走了,她哭了,第一次开口叫了我一声‘老师’。”
苏念眼眶发热。
那天傍晚,她独自登上村后的小山岗。夕阳沉入海平线,将天空染成金紫色。她坐在一块岩石上,取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翻开一页页抄录过的信件、日记、口述记录。这些都是这些年走过的路上收集的“未完成的呼唤”??母亲写给战死儿子的绝笔信、老兵寻找失散战友的录音稿、被拐儿童亲生父母的手绘寻人启事……
她正欲提笔续写,忽觉脚边微动。
低头一看,一株忆尘草正从石缝中钻出,嫩叶舒展,花瓣初绽,蓝得近乎透明。
“你也听见了?”她轻声问。
风拂过耳际,仿佛回应。
就在此时,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晓尘发来的消息,只有短短一行字:
>“北海有灯塔熄了,我们要去修。”
苏念合上本子,深吸一口气。她知道,那座灯塔位于极北海域的一座孤岛上,曾是赵擎年轻时驻守的地方。二十年前,他亲手点亮那盏灯,照亮无数迷航船只。如今灯灭,不只是机械故障,更是某种象征的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