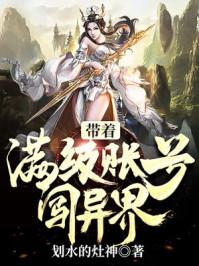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修仙:从装备栏开始 > 第189章 元婴追杀灵宝之威求一下月票马上掉出500名了(第2页)
第189章 元婴追杀灵宝之威求一下月票马上掉出500名了(第2页)
“走。”她收起笛子,语录簿自动合拢,落入袖中,“去长安。”
三日后,二人抵达京城。
昔日繁华街市如今笼罩在诡异的宁静之中。行人步履匆匆,彼此避目而行,偶有交谈也极简短,且每句话出口前都要反复斟酌。茶馆酒肆不再喧哗,学堂里学生低头默读,连孩童嬉戏都只用手势比划。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抑的恐惧,仿佛谁多说一句,就会招来灾祸。
回音塔外排满了前来倾诉之人,却无人真正开口。他们站在塔门前,嘴唇翕动,最终只是深深鞠躬,转身离去。塔内本应流转的净化光流变得黯淡迟滞,宛如垂死者的脉搏。
语疗司大堂内,官员们面色灰败。见到苏晚到来,主事老臣踉跄上前,双手奉上一本漆黑册子。
“这是……三天来各地上报的‘自愿缄口书’。”他声音沙哑,“超过十万份。百姓主动请求取消言语权,换取‘内心的平静’。有些人甚至写下遗嘱,要求死后焚去声带,以免魂魄在冥界继续造业。”
苏晚翻开册子,一页页看下去。有农夫写道:“我说了实话,乡邻便孤立我,不如不说。”
有妇人写道:“我揭发丈夫贪污,他跳河自尽,我害了他,从此再不敢言是非。”
有学子写道:“我批评朝廷政策,被同窗围攻羞辱,方知直言无益,反招杀身之祸。”
每一句话背后,都是活生生的创伤。而这些伤痕,正被无形之手收集起来,酿成新一轮的沉默瘟疫。
“这不是简单的心理创伤。”苏晚合上册子,眼神锐利如刀,“是有人在系统性地挖掘‘言之后果’,并将个别人的悲剧放大为普遍规律。他们在制造一种新的信仰??‘说话必遭报应’。”
当晚,她在语疗司顶层布下“溯言阵”,以忆香炉九盏、共感镜一面、语录簿为引,尝试追溯这些“悔言”的源头。柳知微协助调频,将三十六座回音塔的残响汇入阵心。
随着咒文吟诵,镜面逐渐浮现影像:一片荒芜山谷,中央矗立着一座由碎骨与黑铁铸成的高台。台上站着数十名身穿旧式官服的人,双手高举,口中念念有词。他们的脸模糊不清,唯独额头上的逆承符印清晰可见。
而在高台之下,无数透明人影跪伏在地,正是那些提交缄口书的民众。他们每个人的头顶都飘出一条细线,连接至空中某个看不见的节点??那里悬浮着一枚巨大的、跳动的晶体,形如心脏,色泽暗红,表面刻满扭曲文字。
“那是……‘悔意共鸣核’!”柳知微惊呼,“他们把人们的懊悔炼成了实体能源!”
苏晚死死盯着那晶体,忽然察觉其跳动频率竟与自己腕间胎记完全同步。
“不对……”她喃喃,“这不是外来的术法……这是从‘承言者血脉’中分裂出去的一部分。”
她猛然想起母亲临终前写下的血书:“晚,别怕。”
那不仅是安慰,更是一道封印指令??将一部分关于“言语代价”的沉重认知,剥离出来,藏入时空夹缝,以防年幼的她过早背负全部真相。
而现在,有人找到了那部分被封存的记忆,并将其扭曲为武器。
“是谁?”柳知微问。
苏晚闭目,指尖轻触语录簿封面。书中自动浮现一行新字:
>**“他曾是你最信任的师兄,也是第一个背叛誓言的人。”**
记忆如潮水涌来。
十年前,玄昭书院尚存,她是年纪最小的弟子,而他是首席语匠,名为**谢怀瑾**。他温润如玉,教她辨识古咒,陪她守夜抄录语痕,甚至在她母亲遇难后,抱着她说了整整一夜的话,直到她哭累睡去。
可也正是他,在止语教最后一次突袭中,亲手交出了默使名单,换来了全家性命。事后他消失无踪,传言已死于乱军之中。
原来他还活着。
而且,他早已不再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