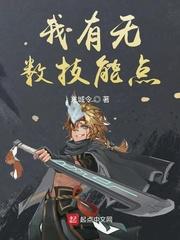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永乐帝后 > 岳父岳母的提醒(第3页)
岳父岳母的提醒(第3页)
徐仪目光清亮,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陛下忌惮的从来不是廖侯一人,而是他身后整个巢湖水师旧部。当年若无巢湖水师归附,便无鄱阳湖大捷,若无鄱阳湖大捷,便无大明今日之江山。”
朱棣眼中闪过赞许,逻辑分明地继续说道:“南京城依长江而建。巢湖水师又唯廖侯马首是瞻,若镇不住他廖永忠,一旦有变,他随时可凭借自身与已故兄长的经营,迅速召集旧部,顺江而下。”
“顺江而下,封锁长江,围困金陵。”徐仪眼中锐光一闪,语声渐冷,“一旦长江水道被锁,漕运断绝,南北不通,这大明,顷刻间就会沦为半壁江山。”
朱棣闻言,脸上难掩惊异。他还是第一次听徐仪谈论兵家之事,竟能如此一针见血。
徐达欣慰的看着两个孩子,长江后浪退前浪,自己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何曾有这些见识。
他微微颔首:“陛下在为太子铺路,他可以容忍一个骄纵的功臣,但绝不能容忍一股无法掌控的力量,随时有可能威胁到国都的命脉。”
“陛下最忌脱离掌控之人。”徐达目光如炬,深深望向徐仪。他今日特意点拨女儿,就是要让她清楚皇帝的心思,朱元璋的心思如今已愈发深沉难测。
他语重心长:“殿下身为藩王,日后少不了与军中将领往来周旋。而我徐家功勋卓著,封无可封,赏无可赏,已至人臣之极。越是如此,越要懂得审时度势,顺应圣意。”
徐达觉得这正是阐明利害的时机,于是话锋一转:“天威难测,唯有谨守臣节,方能保得家族长久平安。”
他看向女儿,开口问道:“你且说说,诛杀廖永忠,于朝政大局而言,究竟还有何深意?”
徐仪垂眸道:“勋贵们这些年联姻结盟,盘根错节,细算起来大多沾亲带故。开国功臣不比寻常武将,号召力不可小觑。陛下杀廖将军意在敲山震虎,这是在教武勋该如何行事、如何效忠。”
朱棣愣了一瞬,有些事父皇和徐叔叔心照不宣,他原以为徐仪也会默契不提。此刻定定望着她,只觉自己又一次低估了她,她从来不是甘居人下的,纵然对方是亲王也一样。听她一语道破政事核心,也点明了他们婚姻的本质,父皇欲借徐家和平收回北平的主导权,徐家也要借皇家,保这世世代代的富贵。
徐达抚须而笑,眼底满是毫不掩饰的自豪,向朱棣朗声道:“殿下,老夫这女儿自幼便未尝以寻常闺阁之礼相拘。兵书策论、权谋心术,无一不可习。殿下能得小女为配,实是天赐良缘,亦是殿下的福分。”
这般言语若是出自寻常臣子之口,未免有僭越之嫌。然徐达功勋卓著,此言由他道来,反倒更显厚重。朱棣闻言,眼底掠过真切的笑意,当即拱手一礼,郑重应道:“徐叔父厚爱,侄儿铭感于心。能得仪儿为妻,定当珍之重之,不负所托。”
朱棣在魏国公府用了晚饭,饭后与徐达又说了几句闲话,便起身告辞。
他穿过游廊,寒气便扑面而来,夹着细碎的雪沫子,像盐粒子似的打在脸上,冰凉刺骨。廊下的灯笼在风中摇曳,昏黄的光晕在雪地上拖出长长的、晃动的影子。就在他即将步出垂花门时,一个身影赶了上来,恭敬地躬身行礼。
“殿下,请留步。”
朱棣定睛一看,是魏国公府的老管事吴廷忠。这老管家在徐家待了快二十年,是徐达的心腹。
“吴管事有事?”朱棣问道,声音在寒夜里显得格外清冽。
“不敢耽误殿下。是夫人的意思。”吴廷忠从袖中取出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素笺,双手奉上,“夫人说,有几句话,想请殿下过目。”
朱棣接过那张薄薄的纸,当场展开,上面写着: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吴廷忠见他看完了,又上前一步,压低了声音,将谢佩英的话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夫人说本不该如此冒犯殿下,只是小姐即将出阁,有些话不得不说。夫人曾有幸亲眼见过马皇后是如何为陛下筹谋军需、镇抚后方。那份胆识,那份智计,至今不敢或忘。”
“也正是从那时起,夫人便下定了决心,要将小姐教导成一个不单能管束后宅,更能辅佐丈夫,安定家国的女子。只要殿下肯信她、容她,给她一片比这深宅后院更广阔的天地,她也一定,不会让殿下失望。”
朱棣捏着那张薄笺,几乎能感受到那墨迹中蕴含的殷切与期盼。他忽然有些好笑,徐叔叔和谢叔母,当真是夫唱妇随,都想到了一处去。一个在堂上借着国事点拨他,一个在堂下遣人私下叮嘱,话里话外,都是一个意思:我这女儿是个宝贝,你可千万别不识货,别把她给埋没了。
可他们哪里知道。
早在他还不清楚娶了徐家女,能给他带来多大助益的时候,就已经想娶徐仪了。
那些所谓的利益、政治、筹码,不过是后来附加上去的锦上添花。他真正想要的,从始至终,就只有一人。
朱棣的脑海里,倏地闪过方才在席间,她垂眸论政时那灵动的神情。他低笑一声,胸腔里漾开一片温热,仿佛世间珍宝,已稳如囊中。
“知道了。”他淡淡地应了一句,“替我转告叔母,她与叔父的苦心,侄儿记住了。”
说罢,他转身离去。高大挺拔的身影很快便跨出了大门,融入了魏国公府外那片苍茫的雪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