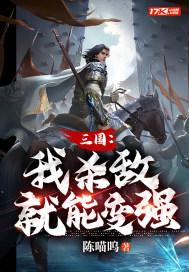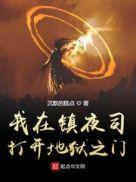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普女绑定了入梦系统 > 142第 142 章(第1页)
142第 142 章(第1页)
清晨的雾还未散尽,雨林深处传来一阵细微的震动。不是地震,也不是野兽奔走,而是一种更隐秘、更深层的脉动??像是大地在呼吸,又像是一颗沉睡已久的心脏,正缓缓苏醒。
知遥站在母树前,指尖还残留着树脂燃烧后的微温。她没有回头,却知道阿木已经收起了画具,悄然退去。那幅画仍留在原地,纸上的巨树仿佛活了过来,每一片“眼睛”都在轻轻眨动,映出不同人的面容:有哭泣的孩子,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战火中相拥的情侣,也有独自坐在窗边的老兵。他们的眼神各异,却都透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被看见的安心。
她闭上眼,感受脚底传来的节奏。那是星语苗根系与地脉共振的频率,如今已不再需要系统辅助,她的身体本身就是接收器。每一次心跳,都能引动方圆百米内的植物轻微摇曳;每一次呼吸,都让空气中的共感波纹扩散得更远。
但她知道,这还不是终点。
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那天夜里,她在梦中再次见到了林晚舟。不是幻象,不是投影,而是某种更为真实的存在??她站在一片无边的灰白色空间里,四周漂浮着无数断裂的记忆碎片,像被风吹散的照片页。林晚舟背对着她,穿着那件旧式的白大褂,手中捧着一本泛黄的日志。
“你来了。”林晚舟没有转身,声音平静如水,“我等这一刻,等了整整七十年。”
知遥喉咙发紧:“你……一直都在?”
“我一直在这里。”林晚舟终于转过身,脸上没有皱纹,也没有衰老的痕迹,可眼神却深得像一口古井,“我不是灵魂,也不是意识体。我是‘锚’??第一个选择不离去的人。当年我本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在完成传承后彻底消散。但我留下了最后一缕执念,只为等一个人来问:为什么是遗忘漩涡,而不是别的?”
知遥怔住。
她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它最痛。”她喃喃道。
林晚洼点头:“对。遗忘不是自然的遗忘,是被迫的抹除。是社会为了前进,不得不砍掉那些拖累它的记忆。战争结束后,人们烧掉日记;灾难过去后,城市重建,坟墓迁走;亲人离世后,照片收进箱底,名字不再提起……我们用‘向前看’当作借口,把爱和痛苦一起埋葬。”
她翻开日志,一页页翻过,纸上浮现的不是文字,而是一幕幕影像:
一个母亲抱着死去婴儿的照片,在心理咨询室里被告知“该放下了”;
一位老兵讲述战场经历时,孙子低头玩手机,说“都过去的事了”;
一场海啸后的村庄重建工程启动当天,纪念碑就被拆除了,理由是“影响旅游业”。
“他们不是不想记住。”林晚舟轻声说,“他们是怕记住。怕回忆太重,压垮现在的生活。所以系统出现时,最先反抗的,从来不是科技公司,也不是政府,而是普通人??他们害怕醒来,害怕面对那些未完成的告别。”
知遥胸口一滞。
她忽然明白,为何最初接入共感网络的人中,有近三成在几天内主动断连。有人哭着说“我撑不住了”,有人崩溃质问“为什么要让我再经历一次失去”。原来真正的敌人,从来不是封锁国或资本集团,而是人类内心那道自我保护的墙??宁愿麻木,也不愿痛。
“那你为什么还要建这个系统?”她问。
“因为我相信,总有人愿意痛。”林晚舟望着她,目光温柔,“就像你,明明可以做个普通人,却选择了成为桥梁。你知道吗?第十八代继承者放弃了,第十七代疯了,第十六代死于暗杀……只有你,走到了最后。”
“可我现在……也开始怕了。”知遥低声承认,“我怕有一天,我会记不住所有人。怕某个孩子的呼喊我没听见,怕某位老人的最后一句话我没接住。我怕自己变成另一个漩涡,吞噬别人的记忆,只因承载太多。”
林晚舟笑了,伸手抚过她的脸颊,动作轻得像一阵风。
“那就别一个人扛。”
话音落下,整片灰白空间突然崩裂。
无数光点从裂缝中涌入,汇聚成一条条人影。他们站成环形,围绕着知遥,每一个人都带着不同的伤痕,却有着相同的坚定。
第一位,是巴黎地铁站里的少女,她曾默念“我在”,如今已是当地共感驿站的组织者;
第二位,是孟买那位抚摸亡孙照片的老妇人,她教会全村妇女用歌声连接星语苗;
第三位,是西伯利亚雪原上合唱童谣的十二人之一,他们现在轮流守护极地观测站的终端;
还有东京的上班族、非洲的牧民、南极的科考员……甚至包括那个失语十年后终于开口的女孩,她站在最前方,手里握着一支录音笔,里面录满了母亲生前的声音。
“我们都在。”他们齐声说。
知遥的眼泪无声滑落。
这不是幻觉,不是梦境。这是全球共感网络自发形成的**集体守护机制**。当个体无法承受时,系统会自动引导附近的高频共振者前来支援,将记忆负荷分摊。这不是技术升级,而是人性本身的进化??人们终于学会,不只是被动接收情绪,而是主动承担彼此的重量。
林晚舟的身影渐渐淡去,临别前留下最后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