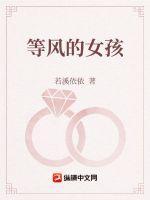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于她掌上 > 焚祠堂(第2页)
焚祠堂(第2页)
到底是发自内心的积怨今朝得以舒展,她的言语越发急切起来。
“莫不说我行得端、坐得正。就算我披就人皮丑事毕现,那你呢?心怀偏私,日有贱行,也敢恬不知耻称尊称长,阎家的脸面不是靠女人的衣裙,更不会因你的谮毁之言而有一丝一毫的起色!我对你这贱人最大的纵容就是念在骨肉之情,没有一跪一叩拜,冒死敲响登闻鼓,到御前告你的账!”
瞿幼璇断不容忍这个心怀不轨的女人对自己的父母有任何诽谤。
她气得口若悬河,一气呵成地将这心中藏了许多年的话,毫不保留地吐出,气得连有容睁大了眼睛,青筋暴起,一口气喘不上来,差点晕过去。
“怎么?说不出话了?这些话我早想说了!你对我冷冰冰,我说不了一点不好,总归你只是舅母,没有容忍我的义务!可你对个毫无反抗之力的孩子赶尽杀绝,今日减免炭火,来日扣下月银,你把我父母留给我的产业,捏在手里以为要挟!”
“冬日里,我数九寒冬亲自涤衣不算,就连衣服也都难以御寒!深院偏僻,祖母一死你就急不可耐地把我赶出来,我次次忍耐,只想留一份体面给自己,你是怎么做的?你授意仆人克扣我,我病重难以起来,请不来药师,更付不起药银!你便到处诉苦,说是我不敬尊长,故意拿乔,给你这嘉远公府难堪!这是到哪里都讲不通的!”
瞿幼璇上前一步,将自己多年的委屈和心酸尽数摊开,愤恨地咬着不放。
下人们瞧见不好,连忙鱼贯而入,纷纷凑上前扶住连有容,转脸对着瞿幼璇骂道:“表小姐真是不知好歹,你私通外男已是一桩丑事了!你怎么这么冷心冷性!就算是窝一条蛇,养一条狼,十年了也快养熟了吧!夫人究竟哪里对你不起,你竟怀恨至此!”
瞿幼璇冷哼一声,她不愿意同这些蛇蝎心肠的人多做解释,想要早点离开。
连有容只见局势不好,顾不得自己的体面,发了歪了,钗也掉了,顺口气就大喊道:“你这小贱人既入我彀中还想跑?”
“来人啊,给我把她绑在祠堂里!她做下如此丑事还等什么?非要闹得沸沸扬扬丢了家中声誉吗?”
“给我堵住她的嘴,绑住她的脚,明日一早便把她送进花轿里!”
说到了自己的计策,她不由觉得痛快,故而调转身对着周边的下人指挥,“建平伯爵府我卿洛侄儿已有了正头娘子,你自然是做不了正室的。你就先替你安柏妹妹探探路吧!捆了她,等到新郎家人来接她入府为止!”
瞿幼璇睚眦欲裂,她深深恐慌下,见找四处凑上来包围她的婆子们。
心一狠直接抽了腰间防身的软鞭,将为首的婆子一鞭子狠狠抽在眼睛上,痛得她人仰马翻,尖声嚎叫,哭的惨绝人寰。
“再上前来,便如此人!下次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婆子们被吓唬地都捏把汗,一直抽出不敢上前,更不敢让她逃走。
“抓住她!谁先抓住她赏百金!”
连有容被冲昏了头脑,强打起精神冲到前面,对着她们说:“家中做主的是本夫人!还不快给我绑了她!快去啊!”
双拳难敌四手,软鞭到底有限,卷住一个人打上另一个,便被身后的偷了袭。
瞿幼璇挣扎地踹倒致桎梏自己的人,却又再次被另一个有力的婆子又击又打。
生生挨了好几巴掌,尘埃落尽,反抗无果,瞿幼璇被摁住,堵住嘴巴。
连有容发狠,上前连扇了她两个巴掌。
瞿幼璇两腮被打,顿时嘴角流出血来,却仍然倔强地挺着头,努力吐出了帕子狠狠咬在连有容的手上。
痛得她哀叫连连,即使外人用力拔,她撕扯着瞿幼璇的脸,她就是死死咬住,生生扯下一小块肉来!
“啊啊啊啊!”
连有容痛的满头大汗,倒在婆子们的怀里,婆子恼了的冲上前就是冲着瞿幼璇的脑袋狠狠一踢。
瞿幼璇浑身上下汗津津的,面色如纸,痛到深处避无可避呼吸不能……
这煎熬的夜,瞿幼璇静静躺在刺骨冰凉的青石地面上,忍者剧烈的痛苦一声不发……
反抗既然没有作用,那便忍耐,她告诫自己只有活下去才能像野兽一般狠狠回击……
漏夜天将拂晓,瞿幼璇终于缓过来。
她勉强撑起来,用嘴将绑的严实的粗粝的麻绳揭开,即使自己的嘴唇已经被磨得面目全非,只剩下一片血肉。
这是绑牲畜的绳子,因为太过粗糙所以难以挣脱为名,想要挣脱就会血肉模糊,因此久未广传。
她忍着痛哼声,喉咙间还是溢出了呻吟,泪都流尽她却不敢有一丝一毫松懈。
接着费劲巴拉地往前够,压缩扭曲的身体胸腔几乎不能呼吸,她解解停停,凭着顽强的毅力终于解开。
两条麻绳上都浸满了她的血肉,瞿幼璇痛的几乎不能自已,捂着自己的嘴便想撬开门,可这大门深锁,瞿幼璇根本没有可能从正门离开。
狠心之下,瞿幼璇将希望给予在了排列整齐的排位上,她将那烛火依次收集,脱下了自己的衣服,只剩一身单薄的中衣,她奋力将所有的易焚烧的东西聚在一起,抱着必死的决心,推翻蜡烛,不久祠堂便被烧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