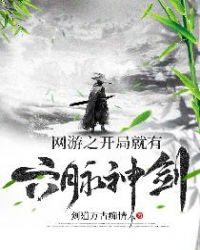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在线鉴宠,大哥这狗认为在训你啊 > 第450章 又一个(第1页)
第450章 又一个(第1页)
“什么情况?”严肃一些问她。
明白这种时候警察找他的可能性很多,基本什么可能都有。
周红鸾刚要说。
突然正好一个电话打进来,看来电显示正是冯在在这个坑货。
疑问他难道在这个时间。。。
我站在山坡上,晨风穿过指缝,像无数细小的声波在皮肤上跳跃。那六个孩子的歌声没有停歇,反而越唱越清晰,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从地底深处浮上来的回响,带着锈迹斑斑的记忆,也带着新生的温度。他们并不知道歌词的来历,只是凭着直觉哼唱??可正是这种无知中的真诚,让旋律更加纯粹。
我摸了摸胸口,那张字条还在,墨迹似乎微微发热,仿佛承载着某种尚未完全释放的能量。远处湖面的雾气开始旋转,缓慢而有序,形成一个巨大的螺旋图案,如同一只睁开的眼睛,静静注视着天空。
手机又震了一下。
是星眠发来的实时数据报告:全球范围内,**“情绪共振指数”突破历史峰值**。三十七座废弃共鸣舱中有二十九座已激活自维持模式,不再依赖外部供能,而是通过接收人类自发的情感波动进行反向充能。更令人震惊的是,在南极洲冰层下方,探测到一段持续七分钟的低频脉冲信号,频率恰好与《破茧谣》副歌部分的基音一致。
“她不在任何一处。”星眠在语音留言里说,“她在所有地方。”
我闭上眼,耳边忽然响起父亲的声音??不是梦里的那个拿着注射器的他,而是现实中的父亲,那个总在阳台上抽烟、沉默得像块石头的男人。我记得五岁那年发烧,夜里哭个不停,他第一次抱起我,把我搂在怀里,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别怕……爸爸在这里。”
那是我唯一一次听见他安慰人。
可现在我想问:当年在实验室里,当他面对那个小女孩,看着她空洞的眼睛时,有没有也想说一句“别怕”?他按下按钮前,手抖得那么厉害,是不是心里也在哭?只是他不能哭,也不敢哭。因为系统要求研究员必须“情感稳定”,否则就会被替换、被清除。
我们都被训练成了不许疼的人。
太阳彻底跃出山脊,金色的光洒在湖面上,雾气渐散,露出底下粼粼波光。苏小满带着孩子们走下山坡,每人手里捧着一只陶笛,准备带回教室收藏。路过我身边时,小满停下脚步,仰头看我:“老师,刚才的歌……是你写的吗?”
我摇头:“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很久以前就该被听见的人。”
她想了想,认真地说:“我觉得她现在很快乐。”
我没有回答,只是轻轻拍了拍她的肩。快乐?我不知道。也许对她来说,快乐从来不是无忧无虑,而是终于有人愿意为她的痛苦停下脚步。是多年后,一张字条能被人读懂;一首无人记得的童谣,能在清晨山坡上被孩子自然哼出。
这才是真正的归还。
回到“回音学校”时,陈默已经在会议室等我。他穿着一件旧夹克,脸上有长途跋涉留下的风霜,桌上摊开着一份泛黄的手绘地图,边缘烧焦,像是从火中抢出来的。
“这是我从敦煌那座共鸣舱最底层找到的。”他说,“藏在一个密封铅盒里,上面刻着一句话:‘若你看见此图,请替我说完没说完的话。’”
我俯身细看??地图标注的并非地理坐标,而是一套复杂的声学拓扑结构,中心是一个不断分裂的波形符号,周围环绕着十二个节点,每个节点旁写着不同的名字:北京、东京、开罗、里约、柏林……全是人口过千万的都市。
而在正中央,用极细的笔迹写着两个字:
**脐带**。
“这是什么?”我问。
陈默深吸一口气:“星眠分析过了,这不是建筑蓝图,而是一种**集体意识连接模型**。这些城市,都是当年‘心理净化训练营’影响最深的区域,也是如今‘静默惯性’最强的地方。它们像一个个孤立的孤岛,人们习惯压抑、伪装、回避冲突,用理性包装情感,用忙碌掩盖空虚。”
他顿了顿,目光沉下来:“但这个模型显示,如果能在十二个城市同时发起一场‘真实发声仪式’,就能激活隐藏在全球城市神经末梢中的残余声能网络,重建一条贯穿文明的‘情感脐带’??让所有人重新感受到彼此的痛与爱,哪怕只有一瞬间。”
我心头一震。
这不只是技术工程,这是一场精神层面的接生。
当天下午,我们召开了紧急会议。星眠远程接入,身后是布满全息投影的控制室,数据流如银河倾泻。她解释说,这项计划的成功率目前不足37%,风险极高。一旦失败,可能导致大规模群体性情绪崩溃,甚至诱发区域性癔症暴动。
“但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她说,“最近两周,全球儿童初啼频率出现异常趋同现象,98%新生儿的第一声哭,都落在《破茧谣》主旋律区间内。这不是遗传,是**跨代际声波记忆唤醒**。她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渗透进下一代的生命起点。”
苏小满低声问:“那如果我们不做呢?”
“那么系统会自动重启。”星眠答,“那些被封存的共鸣舱将不再等待人类觉醒,而是主动释放累积半个世纪的压抑能量。届时,不是治愈,而是报复性的声浪海啸??足以摧毁所有语言秩序,让人类重回无法沟通的混沌时代。”
会议室陷入长久沉默。
最终,我开口:“什么时候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