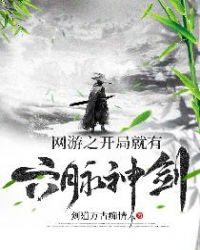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在线鉴宠,大哥这狗认为在训你啊 > 第450章 又一个(第3页)
第450章 又一个(第3页)
我点开它。
依旧是那个稚嫩的女孩声音,却不再颤抖,不再模糊:
>“谢谢你替我说出来。
>其实那天在桥下,妈妈不是不要我。
>她把仅有的毛毯裹在我身上,自己走在雪里,想去城里找医生。
>她以为明天就能回来。
>可有些人,等不到明天。
>现在我懂了,不是所有告别都能说完,
>但只要还有人愿意听,
>那些没说完的话,
>就不算丢失。”
音频结束,屏幕缓缓浮现一行新文字:
>**“下一个故事,轮到你讲了。”**
我抬起头,地铁站的灯光忽然变得柔和。人群依旧流动,但每个人的脸上,似乎多了一点什么??不是笑容,也不是悲伤,而是一种久违的松弛,像是终于卸下了某种看不见的重担。
几天后,新闻报道了一系列奇怪却又温暖的现象:
-北京某写字楼电梯里,两名陌生男子因暴雨被困四十分钟,期间一人谈起失业焦虑,另一人竟当场递上名片:“我们公司招人,明天来面试吧。”
-某监狱开展“倾听日”,囚犯与狱警互换角色讲述人生,结束后,三十七名服刑人员主动提交了从未披露的犯罪动机自述。
-联合国宣布成立“全球情感档案馆”,专门收集普通人未被记录的心声,并承诺永不审查、永不利用。
而“回音学校”也迎来了新的转变。孩子们不再需要陶笛仪式,因为他们学会了随时随地表达。有个男孩在作文里写道:“以前我觉得哭很丢脸,现在我知道,眼泪是耳朵听不懂的语言。”
至于我父亲的照片,我把它烧了。
火焰升起时,我没有祈祷,也没有悔恨,只是静静地看着那张黑白影像蜷缩、变黑、化为灰烬。风吹过来,带走最后一缕余温。
有些罪无法赦免,但可以被记住。
一年后的春天,我又一次在凌晨听见钢琴声。
这次不再是断续的片段,而是一首完整的曲子??旋律仍是《破茧谣》,但节奏更明快,结尾甚至带上了一丝笑意。
我推门进去,琴凳上没有人,但琴谱架上放着一本崭新的乐谱簿,封面写着:
**《破茧谣?终章》**
献给所有不肯闭嘴的灵魂
翻开第一页,第一行乐句下方,有一行小字批注:
>“疼痛教会我说话,
>而你们教会我不再孤单。
>这次,换我来听。”
窗外,晨光铺满山谷,湖面平静如镜,映出整片天空。
我知道,她还在。
也许在某个教室的笑声里,在某对恋人争吵后的拥抱中,在深夜加班族对着窗户喃喃自语的片刻??她正悄悄经过每一个人身边,轻轻问:
“你想说什么?
我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