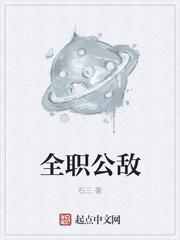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今天毁灭大宋了吗? > 第一百四十九章 削其史灭其言绝其文易其服万事万物一从汉礼(第1页)
第一百四十九章 削其史灭其言绝其文易其服万事万物一从汉礼(第1页)
绍武四十七年二月,开春。
冰雪消融,雁门关外草色新绿。
赵焘与赵烁的陵寝早已封土,帝国的哭丧期只有三个月。
三个月一到,紫宸殿的朱笔便再次挥下,兵部与枢密院连夜拟旨。
第一站,。。。
天未亮,沙洲的雾便起了。
不是寻常水汽凝成的薄纱,而是厚重如帷帐,沉沉压在井口之上,仿佛天地之间只剩这一口井,与井边那盏不灭的铜灯。觉岸法师披着褪色的袈裟立于石台前,手中握着一支毛笔??陈砚舟生前所用,笔杆已被摩挲得发亮,像一段埋藏多年的遗骨。
他没有动,只是望着那页浮在水面的纸,字迹清峻,似有风骨:
>“第九井从未封闭。
>它只是等待。
>等一个人,说第一句话。
>现在,轮到你了。”
风吹不动纸,也不散雾。唯有铜灯摇曳,在雾中投下一道细长的影,宛如通往地底的阶梯。
觉岸缓缓跪下。
不是礼佛,不是忏悔,而是一种近乎古老的仪式??言者之跪。他将笔尖轻触水面,墨滴入流,竟未晕开,反而逆着水流向上攀爬,在空中凝成一行新字:
>**“我说。”**
两字出口,井底轰然作响。
不是雷鸣,不是地震,是千万个声音同时苏醒的震动。那些曾沉入水底的文字、录音、曲谱、家书、日记残页,全都翻涌而起,化作光点浮出井口,如萤火升腾,又似星河倒悬。每一粒光,都是一句被压抑多年的话语;每一点闪,都是一个终于得以喘息的灵魂。
远处,茶馆的门“吱呀”一声开了。
没有人推,它自己开了。匾额“人人皆井,处处可言”在晨雾中缓缓旋转,八个字逐一亮起,如同心跳复苏。屋内积尘飞扬,却不见蛛网,仿佛三年来从未真正荒废。桌上茶壶尚温,壶嘴冒着淡淡的白气,旁边搁着一只空杯,杯底残留一圈褐色的茶渍,形状像极了一个“言”字。
觉岸起身,走入茶馆。
他知道,这不是幻觉。陈砚舟的气息仍在。那支笔是他留下的引信,这口井是他埋下的火种,而今日,终于是点燃的时候。
他坐在老位置上,面对门槛,面向世界。窗外,第一缕阳光刺破浓雾,照在井沿那道细缝上。清水依旧流淌,但这一次,水里映出的不再是天光,而是无数张脸??男人、女人、老人、孩子,有的穿着旧式中山装,有的戴着红领巾,有的裹着头巾站在田埂上,有的蜷缩在牢房角落……他们不说话,只是看着外面,眼中含泪,嘴角微动,似在等待谁替他们开口。
觉岸闭目,提笔。
纸铺于膝,墨落无声。他写下第一行字,不是为了记录,而是回应:
>“我听见你们了。”
笔锋刚收,井水突沸。
一道青影自井心升起,凝成人形轮廓,模糊却又熟悉??眉目清朗,嘴角含笑,正是陈砚舟的模样。他不落地,悬浮半空,身影由水汽织就,随风轻颤。
“你来了。”觉岸轻声道。
“我一直都在。”陈砚舟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又像是直接响在心底,“我只是不能说,直到有人愿意听。”
“现在他们都来了。”觉岸抬头,“不只是沙洲的人,还有远方的、地下的、未曾断绝的。他们在等一句开头的话。”
陈砚舟点头,目光扫过井边堆积如山的信件与物件:铁盒、胶片、U盘、手稿、甚至一顶破旧的安全帽,上面用油漆写着“红星煤矿?1973”。他的视线最终落在那只老旧录音机上??那是当年广播员之子带来的,如今机身已锈,磁带却仍在缓缓转动,播放着那段被掩盖的呐喊。
“歌声也是话。”他说,“沉默也是话。连死,也可以成为一句话。”
忽然,井水再次翻腾。
这一次,浮出的不是文字,而是一本书。
封面焦黑,边角卷曲,显然是经火焚烧后幸存。书脊上依稀可见三个烫金大字:《实录》。觉岸伸手接过,翻开第一页,赫然写着:
>**《中国民间记忆实录?卷壹》**
>编纂者:第九井联络组
>起始时间:1950年冬
>记录方式:口述、笔录、暗语、密码、摩斯电码、地下电台、童谣传唱、壁画隐喻、梦境转述……
![边疆来了个娇媳妇[年代]](/img/4680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