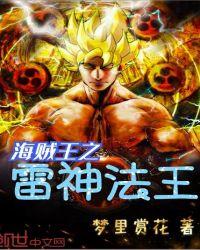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晋末芳华 > 第五百三十五章 城破大乱(第1页)
第五百三十五章 城破大乱(第1页)
而东门那边,得知报信的桓温,也做出了相同的决定。
他同样派了一万援军,由桓石虔率领,援助南门,同时发令其他人猛攻东门。
这无形中的默契,一下就超过了邺城守军的极限,城头值守的兵士根本无法抵。。。
海风拂过山腰的杏树林,花瓣如雨飘落,在湿漉漉的石阶上铺成一片淡粉。小满的手指仍停留在琴弦上,最后一个音符缓缓消散于空气之中,仿佛融入了细雨与花香。母亲的头靠在她肩上,呼吸轻得几乎听不见,可那手掌却紧紧攥着她的手腕,像是怕一松手,眼前的一切就会化作幻影。
许久,母亲才颤声开口:“你长高了。”
声音沙哑干涩,像久未开启的门轴,却让小满心头猛然一震。这句再普通不过的话,竟比任何深沉的告白更让她泪崩。她咬住嘴唇,不敢哭出声,只任泪水顺着脸颊滑下,滴在昭华琴的漆面上,映出两人的倒影。
“您瘦了。”她终于挤出一句话,嗓音哽咽。
母亲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深深绽开,如同枯枝逢春。“活下来的人,总是要瘦一点的。”她说着,慢慢弯腰捡起掉落的录音机,手指抚过那布满划痕的外壳,“这是你七岁那年,我用三个月口粮换来的。你说想学唱歌,可家里连收音机都没有……我就把它带回来了。”
小满怔住了。她记得这台机器??小时候每晚睡前,母亲都会放一段简陋的电子旋律,说是“远方电台的节目”。原来,那是母亲一遍遍录下的自己哼唱的歌。
“您一直在录?”她问。
“嗯。”母亲点头,“哪怕后来他们割了我的声带,我也用手指敲节奏,记在纸上。只要还能动笔,我就没真正失声。”
小满猛地抬头,目光落在母亲脖颈处那道狰狞的疤痕上。她从未想过,一个人能在失去发声能力后,仍以如此倔强的方式守护声音。
“所以……您听见了我的琴声?”她轻声问。
“一开始只是模糊的感觉。”母亲望着远处云雾缭绕的山谷,“但有一次,广播里播放赎忆堂的纪念音乐会,你的演奏传到了边境信号站。那一刻,我忽然认出了那个转调??你总是在第三小节多拖半拍,和小时候一模一样。”
小满闭上眼。那是母亲教她的第一首曲子《杏花谣》里的习惯性错误,曾被她反复纠正,却始终改不掉。如今,这“错误”成了她们重逢的密码。
雨又下了起来,细细密密,打在屋檐上发出清脆的嘀嗒声。护工悄悄走来,轻声提醒该回房休息了。母亲却不肯起身,执意要再听一首。
“弹那首……你在邮件里写的歌。”她说。
小满微微一愣。那首新曲尚未完成,甚至连名字都没取。但她还是点了点头,将琴重新抱稳,指尖轻轻拨动。
旋律起初缓慢而试探,像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脚步。然后,低音部缓缓升起,带着压抑多年的思念与委屈;中段转入明亮的小调,夹杂着孩童时期的欢笑片段;最后,一个全新的副歌悄然浮现??那是她在船上某夜梦见的旋律,像母亲的手轻轻拍着背,又像风穿过杏树梢头。
母亲听着听着,忽然跟着哼了起来。虽然音准不稳,喉咙颤抖,甚至几次破音,但她坚持着,一字一句,仿佛要把二十年的沉默都补回来。
当最后一个音落下,整个世界似乎安静了一瞬。
随即,院中一棵老杏树上的鸟巢里,一只幼鸟扑腾着翅膀,发出稚嫩的鸣叫。紧接着,另一只回应,再一只加入……清脆的鸟啼此起彼伏,宛如一场自发的合唱。
小满笑了,眼泪却止不住地流。
当晚,她在康复中心安排的客房住下。房间陈设简单,墙上挂着一幅手绘地图,标注着全球几个共感疗养点的位置,其中一处正是启言城。她走近细看,发现角落还写着一行小字:“等女儿回来时,我要亲自告诉她,妈妈没有逃。”
她站在那里良久,直到窗外月光洒进来,照在床头那本翻开的笔记本上。那是母亲的日记,护工说最近才开始写。第一页写着:
>“今天,我看见了她。
>她背着我的琴,穿着我织的毛衣(虽然已经太小),站在雨里对我笑。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握住她的手。
>可那一瞬间,我明白了:
>所有的苦难,都不是为了让我恨这个世界,
>而是为了让我更用力地爱她。”
小满合上本子,走到窗前。夜空中,极光悄然浮现,淡淡的绿芒在天际流转。南极科考站的数据同步显示,今晚的共感共振波达到了近期峰值,源头无法定位,但频率特征与昭华琴的共鸣基频高度吻合。
她知道,这不是巧合。
第二天清晨,她早早起床,抱着琴来到庭院。母亲已在石凳上等候,身旁摆着一杯热茶。阳光透过薄云洒下,杏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我想教您弹那首新歌。”小满说。
母亲摇头:“我现在……很难控制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