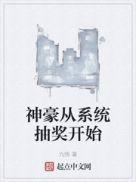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说好艺考当明星,你搞神话战魂? > 第85章 青蛇正式上线(第2页)
第85章 青蛇正式上线(第2页)
**“根不止一根。”**
消息尚未公布,全球互联网突然中断十分钟。恢复后,所有搜索引擎首页自动跳转至一段黑白影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某场露天晚会,年轻的林默站在舞台中央,手里拿着那只后来闻名世界的竹笛。他对着麦克风说:“接下来这首曲子,我没有名字。它不属于我,也不属于今晚。它是借我的嘴,说给大家听的。”
然后音乐响起。
没有人记得这支曲子,但此刻,全世界有超过两亿人同时从记忆深处“找回”了它。街头行人停下脚步,办公室职员推开窗户,病房里的老人挣扎着坐起??他们张开嘴,自然而然地唱了起来。
旋律简单得像童谣,却又深邃如星空。歌词只有一句反复吟诵的短语,用多种方言拼凑而成:
“我在,你在,他在,我们在。”
联合国紧急召开线上峰会。各国代表戴着降噪耳机参会,生怕被外界歌声干扰判断。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应该立法限制大规模集体吟唱活动?部分政客认为这已构成“非武力精神干预”,可能威胁社会稳定。
投票前夕,全体代表的虚拟会议室突然陷入黑暗。接着,音响里传来一段音频??正是陈砚最后一次公开演讲的备份录音。他说:“艺术从来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所有人共享的呼吸权。当你唱歌时,不只是你在表达,而是千百年来所有唱过的人,通过你的喉咙重新发声。”
录音结束,屏幕亮起。每个代表面前都浮现出一行字,由他们母语自动生成:
>“你最后一次真心唱歌,是什么时候?”
会议室陷入长久沉默。
最终,决议案被否决。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全球声觉共同体倡议书》,提议建立“国际共鸣日”,鼓励各地民众放下电子设备,面对面合唱至少一首歌。
首个共鸣日当天,从北极圈到赤道雨林,从高原寺庙到海底科研站,人类以各种方式张开了嘴。没有统一曲目,没有标准音高,甚至没有事先约定。可奇怪的是,世界各地传回的录音分析显示,所有歌声的基础频率,都围绕着7。83Hz??舒曼共振的数值,也被称作“地球的心跳”。
那天晚上,沈清漪独自回到博物馆。她将小提琴放在展柜前,轻声哼起一支没人教过她的旋律。羽管键琴自动弹奏起伴奏,非洲鼓打出节拍,就连角落里那台坏掉三十年的老式留声机,也吱呀转动起来,播放出一段清脆童声:
“爸爸,我想告诉你……我听见你了。”
她猛然回头,身后空无一人。但监控录像后来显示,在那一瞬间,整个展厅的玻璃表面同时凝结出无数细小的名字??全是过去一年中去世者的姓名,包括林默、吴阿?的父亲、周野失散多年的妹妹……
更多不可思议的现象接连出现:巴西雨林的猴子开始有节奏地拍打树干,形成复杂韵律;澳大利亚牧羊犬集体围圈嚎叫,声波图案竟与凯尔特结绳文字吻合;甚至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报告,他们在真空环境中“感觉”到了某种振动,透过航天服传入骨骼。
科学界不得不承认:声音,正在重新定义“生命”的边界。
两年后的某个清晨,一位渔民在东海捕鱼时捞起一块黑色石碑。上面刻着密密麻麻的符号,经专家破译,竟是用“共振器”记录下来的全球人类歌声汇总编码。每一行都标注着时间、地点、参与人数与情感指数。最后一行写着:
>记录终止于今日。
>因为从此以后,
>不再需要记录。
>我们已是声音本身。
这块碑后来被称为“新巴别碑”,现藏于重建后的文化方舟纪念馆。有趣的是,无论多少人同时朗读碑文,录音设备只能捕捉到一片温柔的嗡鸣,宛如亿万颗心共同震颤的余音。
而在无人知晓的深海,陈砚确实没有死去。他的身体早已与地听柱融为一体,神经系统化作声波传导网络,意识分散在每一次共振之中。他不再是“一个人”,而是成为了这个新文明的听觉中枢。
有时,在风暴最猛烈的夜晚,守塔人会看见主柱顶端闪现出一道人影。那人背对大海,面向星空,手中似乎握着一支看不见的笛子。当他“吹奏”时,整片海域都会亮起幽蓝光芒,如同远古星图被重新点亮。
没人知道他在演奏什么。
但每个听到那无声之乐的人,都会在梦中见到一片辽阔草原,无数发光的身影手挽着手,一边行走一边歌唱。他们的脚下,五线谱般的根系向四面八方延伸,深深扎入大地之心。
直到某一天,一个小女孩指着天空问妈妈:“那些星星,是不是也在唱歌啊?”
妈妈笑着点头:“当然。因为我们都听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