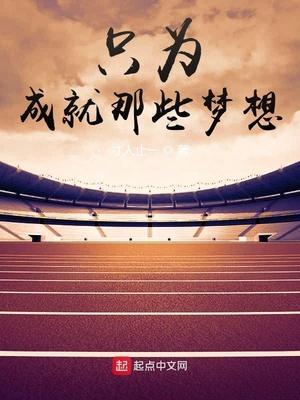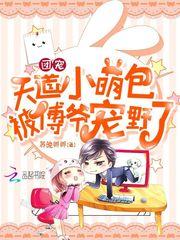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她靠噬恶念破案 > 红绳(第4页)
红绳(第4页)
“邻居都说至少三天没见着她人影了。一个天天出门发传单找狗的人,突然连着三天没动静……”
电话那头,贺黎筠的声音比白天更加沙哑,带着几分疲惫。
“技术科做了初步的容貌修复,与周茹的照片高度相似。我们正在调取小区监控,也已经联系她父母做DNA比对。虽然还没出结果,但基本确定是她了。”
薛宓的眉头越簇越紧,贺黎筠说的每一个细节都在印证她最坏的猜想。但此刻她最关心的不是死者身份,而是……
“这红绳的手法是不是那个连环杀人犯?”她迫不及待地问出声。
贺黎筠迟疑了片刻,摇头道:“不是。”
“手法确实很像。同样的红绳,同样的捆绑方式。但有个关键区别,当年的凶手把尸体像展览品一样丢在城郊各处,根本没打算藏,反映出明显的仪式性特征。而这个凶手费尽心机沉尸河底,想要毁尸灭迹,明显在抛尸方式上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心理动机。”
“这种犯罪手法的矛盾性很典型。模仿了最具视觉冲击力的红绳捆绑,却在抛尸策略上展现出规避侦查的理性思维。这正是模仿犯罪最显著的特征,既想复制轰动效应,又缺乏原案凶手的特定心理需求。”
他话语间透着凝重:“当年的核心案件细节,尤其是红绳的特殊捆绑手法、受害者特定物品的缺失,这些关键信息虽从未对外公开,但三年前,有记者泄露了部分现场照片,加上案件一直未破,导致近几年在论坛上的讨论热度一直居高不下,出现了大量所谓的案情还原帖和凶手心理分析。总有人沉迷于解构它,甚至……崇拜它。”
“所以,出现模仿者的可能性很高。”
“监控那边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再响起时,贺黎筠的声音明显沉了下来:“发现浮尸的地点在一段三不管的河道。去年河道清淤时,南岸最后的几个老旧监控探头都被拆除了。新规划的安防系统因为产权纠纷,街道、河道管理处和开发商互相扯皮,预算一直批不下来,导致这块成为了监管盲区。”
“更麻烦的是,这片河道紧邻住宅区,傍晚常有居民散步遛狗,白天还有钓鱼的人,人员流动性大,背景复杂。”他嗓音里压着烦躁,“我们现在唯一能调取的,只有三公里外主干道上的交通卡口监控。”
薛宓仿佛能看见电话那头贺黎筠紧锁的眉头和抿成一条直线的嘴唇——那是他遇到棘手案件时特有的表情。
“2020年了,不是2005年。”他的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怒意,“能找到这样的监控死角抛尸,说明凶手要么极其熟悉当地环境,要么就是做了相当周密的准备工作。”
“等DNA比对结果出来,我们就重点排查死者的社会关系。等有了嫌疑人,或许你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些什么。”
按办案惯例,这类女性被害案首先都会考虑情杀方向。而今天,贺黎筠初步排查发现,周茹是独居状态,父母口中并无交往对象,邻居们也纷纷表示从未见过有男性访客。
而公司同事也均证实她近期没有恋爱迹象,作为新人也没有职场纠纷。周茹的生活简单到近乎单调,每日往返于公司和住所,这让情杀与仇杀的可能性大幅降低。
若是监控能捕捉到可疑身影,让薛宓进行辨认,案件或许能有突破。但自DNA确认身份后,调查组查遍了周茹搬来后的所有监控,发现她在爱犬走失后,整天举着寻狗启事在小区内外奔走。
快递员、外卖小哥、遛狗居民、物业保洁、甚至路过的好奇孩童……接触人员繁杂得像一团乱麻。
更棘手的是,案发三天后,周茹的手机依然杳无音信。
而贺黎筠也终于调取到了她的通话记录。
正因为寻找爱犬,她最近一个月的通话记录里密集出现了上百个陌生号码——宠物店、流浪动物救助站、小区业主、声称看到相似狗狗的热心人、还有多个冒充拾到狗狗的诈骗电话。
每个号码都需要交叉核验身份背景、排查通话时长、追溯基站定位……给排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度。
唯一能确定的是,周茹的死亡时间推测是在8月20日晚上九点半到十点半之间。手机信号最后消失的基站位置,恰好就是发现她尸体的那片河道。
从周茹居住的玫瑰花园步行到河道仅需三十分钟,但这对一个独居的年轻女性而言,晚上十点独自前往如此偏僻的地点实在反常。
除非——
她是被约过去的。
可偏偏,通话记录显示当晚并没有任何可疑来电。
就在贺黎筠刚签完调取短信和微信记录申请单,准备递交技术科时,他突然接到了妈妈的电话。
他工作繁忙时妈妈很少来电,他心头莫名一跳,就听到电话里传来妈妈紧张的声音:“小筠,妈同事群里都在传……河里发现的那具女尸……是不是十六年前那个杀人犯又出来了?”
贺黎筠心中咯噔一下,语气不自觉地带上刑警审讯时的锐利:“妈,案件还在保密侦查阶段,所有信息都是内部资料。你同事具体是怎么说的?原话是什么?消息源头是哪个平台?”
电话那头的崔芳华被儿子罕见的严厉语气惊到,迟疑了几秒才说:“就……就在部门群里看到的链接,说是微博上都在传……还配了打了马赛克的照片……”
贺黎筠立刻点开微博。
根本不需要搜索——#青江连环杀人魔重现#的词条就赫然挂在热搜榜首,后面跟着一个暗红的“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