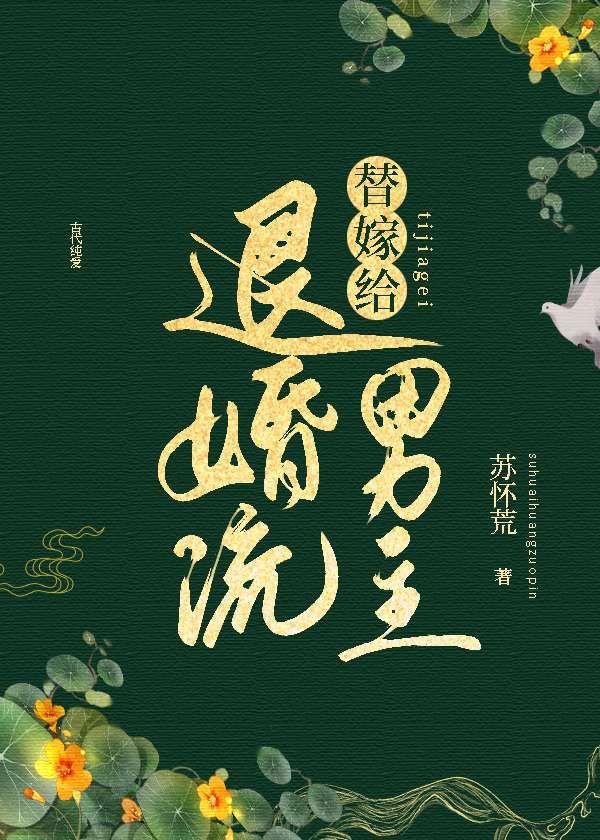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展昭传奇 > 第一百三十九章 出世为戒色入世为展昭(第2页)
第一百三十九章 出世为戒色入世为展昭(第2页)
回到总部那天,正值“清明诵读日”前夕。回音塔前已排起长队,人们手持丝带,等待将自己的话语悬挂其中。小女孩站在志愿者队伍里,正帮一位盲人老人誊抄他的回忆录片段:“我亲眼看见征地办的人把李阿婆拖出房子,她手里还抱着孙子的照片……”
少年走上前,轻轻抱住她肩膀。
“叔叔!”她惊喜回头,“你回来了!我们都以为你出事了!”
他笑了笑,没解释太多。“我想请你帮我做件事。”
“你说。”
“我要在全国设立一百个‘说话角’??不在学校,不在广场,而在菜市场、公交站、医院走廊、工地休息棚。地点越平凡越好,形式越简单越好。不需要演讲台,只要一块可写字的黑板,一支粉笔,一本留言册。名字就叫:‘我说话了’。”
女孩眼睛亮了起来:“就像展昭爷爷那样?”
“比他更进一步。”他说,“他是在孤灯下写给未来的信。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让每个普通人随时随地都能开口。”
计划很快启动。第一块“说话角”出现在东江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候诊区。起初没人敢写,直到某天清晨,有人在黑板上留下一句话:
>“我妈等肾源等了两年,昨晚死了。医生说,有个领导家属三天就配上了。”
这句话停留了一整天,没人擦,也没人回应。第二天,下面多了一行字:
>“我也在等。我不认识领导,但我记得你妈妈的名字。”
第三天,又添一句:
>“我是值班护士。我知道名单有猫腻,但我一直不敢说。今天,我说了。”
一周后,这块黑板被拆除,警方介入调查。但与此同时,照片已传遍网络,十七个城市自发出现了类似的“说话角”。有人贴发票证明药价虚高,有人画图揭露学区房骗局,还有退休警察写下当年被迫结案的冤案细节……
察言司再次出手,发布《关于整治公共场所非法言论设施的通知》,要求全面清理未经审批的公示栏、留言板、涂鸦墙。城管开始每日巡查,粉刷墙壁,没收粉笔。
可人们学会了新的方式。
菜市场卖鱼的大妈,在秤盘底下贴小纸条:“今日鲫鱼新鲜,政府通报的CPI不包括活鱼。”
快递柜屏幕上,取件码变成暗语:“3691??疫苗接种率造假,请查疾控中心内部邮件。”
连街头乞丐的破碗里,也被发现压着一张字条:“我不是懒,是工厂倒闭后没人给我工伤赔偿。”
语言,正在以最日常的方式突围。
半年后,太子病倒,朝局动荡。新任监国皇子年少气盛,意图铁腕整顿“民间妄议”,下令组建“正言卫”,专司清查一切非官方信息发布渠道,并推行“信用言语体系”??公民发表言论将计入社会评分,散布“未经证实信息”者限制出行、子女入学受限。
政策甫一出台,便引发剧烈反弹。
最激烈的抗议来自教育界。数百名教师联名致信典籍院:“若连课堂讨论都要被评分监控,那孔子也该被判为危险分子。”更有学生集体罢课,在校园墙上刷下巨幅标语:
>**“思想不是商品,不能用积分兑换自由!”**
与此同时,一场意想不到的技术反击悄然展开。
一群匿名程序员开发出一款名为“回声”的去中心化语音存证APP。用户只需录制一段话,系统便会自动将其拆解成无数碎片,加密后分散存储在全球志愿者提供的闲置硬盘中。除非集齐所有碎片密钥,否则无法还原完整内容;而一旦原作者遭遇不测,程序将自动触发“遗言释放协议”,向预设联系人发送录音包。
短短一个月,注册用户突破百万。有人上传自己被强拆的过程录音,有人留存医疗事故证据,还有母亲悄悄录下孩子问:“妈妈,为什么电视里说大家都幸福,可我们吃不上肉?”
察言司技术部门试图追踪服务器位置,却发现这些数据像风中的灰烬,飘散在世界各地的私人设备里。他们查封一台机器,换来的是十万个节点自发复制备份。最终,首席技官在内部报告中写下绝望之语:
>“我们面对的不再是信息传播,而是一种**信念的病毒式生长**。它不怕封锁,因为它本就在地下;它不怕删除,因为它早已分散重生。”
这一年冬天格外寒冷。京城大雪封门,宫墙内外积雪盈尺。某夜,一名小太监在清扫御花园时,发现梅树根部被人埋下一枚铜管。打开后,里面是一段微型胶卷,经投影仪放映,竟是林婉儿在狱中用饭粒粘在草纸上的手写信:
>“他们剪了我的头发,锁了我的手,可剪不断我想说的话。
>我每天都在默背那些被删的文章,一遍又一遍。
>如果有一天我能出去,请告诉外面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