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皮小说网>尸言证词 > 旧案余音font colorred番外font(第1页)
旧案余音font colorred番外font(第1页)
结案带来的平静并未持续太久。一份来自最高检的案情通报和随之而来的内部评审通知,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
通报涉及七年前,由蔺才离主导心理侧写的一起跨省系列抢劫杀人案。当年案件顺利告破,主犯伏法。然而,最近在审理另一起无关案件时,一名在押人员为求减刑,爆出惊人内幕:当年伏法的那名“主犯”,很可能只是其中一个犯罪团伙推出来的替罪羊,真正的首脑及部分核心成员至今逍遥法外,并且,该团伙的作案模式在近几年有死灰复燃的迹象。
通报要求当年所有参与案件侦办的主要人员,尤其是负责核心侧写和定性的蔺才离,接受内部评审委员会的质询,并协助重启调查。
消息传到霖市刑侦支队时,司编年正在批阅文件,笔尖在纸上顿住,洇开一小团墨迹。他抬起头,看向对面办公桌后的蔺才离。
蔺才离显然也刚刚得知消息,他面前摊开着一本卷宗,目光却并未落在纸页上,而是定定地望着虚空中的某一点,脸色比平时更加苍白,下颚线绷得极紧。他放在桌面的手,指节因用力而微微泛白。
七年前。那不仅是青石巷案的时间点,也是这起跨省大案的时间点。那是蔺才离作为犯罪心理侧写师声名鹊起的时期,也是他独自背负着画室火灾秘密、与司编年尚且隔着无形屏障的时期。
“才离。”司编年放下笔,声音沉稳地唤了一声。
蔺才离像是被从某种冰冷的回忆中惊醒,睫毛颤动了一下,视线缓缓聚焦,落在司编年脸上。他没有说话,只是那双深邃的眼眸里,翻涌着复杂难言的情绪,有凝重,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甚至还有一丝司编年从未见过的、类似于……自我怀疑的阴影。
当年他的侧写,如果真的出现了如此重大的偏差……
司编年站起身,走到他桌前,双手撑在桌沿,身体微微前倾,形成一个带有保护意味的姿态。“怎么回事?”他问,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支持。
蔺才离闭了闭眼,再睁开时,眼底的情绪已被强行压下,恢复了惯常的冷静,只是那冷静之下,是深不见底的寒潭。“当年的侧写,基于有限的现场证据和嫌疑人供述。如果存在顶罪和刻意误导……”他没有说下去,但意思很明显。
犯罪心理侧写并非万能,它极度依赖于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一旦基础信息被污染,再精妙的侧写也可能偏离靶心。
“评审委员会什么时候到?”司编年问。
“后天。”
时间紧迫。
接下来的两天,蔺才离几乎不眠不休,将自己重新埋进了七年前那起跨省案的浩淼卷宗里。他需要重新审视每一个细节,每一份证词,寻找当年可能被忽略的蛛丝马迹,或者,证明自己侧写的合理性。
司编年没有过多打扰他,只是默默地承担起了更多的支队日常事务,确保他能有完整的时间投入复查。他会在深夜端着热牛奶走进分析室,放在蔺才离手边,然后坐在不远处的沙发上,处理自己的文件,无声地陪伴。
有时,他会抬起头,看着灯光下蔺才离清瘦而专注的侧影。那人眉头紧锁,指尖快速翻阅着纸张,偶尔会停下来,用笔在纸上写下密密麻麻的批注,那专注的神情里,带着一种近乎偏执的认真和……一丝不易察觉的脆弱。
司编年的心微微揪紧。他知道,蔺才离看似冷静,实则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不仅关乎他个人的专业声誉,更关乎可能存在的司法不公和潜在的继续危害社会的罪犯。
评审会那天,气氛严肃。不大的会议室里坐着几位来自上级机关和兄弟单位的资深专家,目光锐利。蔺才离独自坐在长桌的一端,面前摆放着厚厚的复查报告和原始卷宗。他穿着熨帖的衬衫,领口扣得一丝不苟,面容平静,只有微微抿紧的唇线泄露了他内心的不平静。
司编年作为支队长,也列席会议,坐在旁听的位置。他的目光始终落在蔺才离身上,带着无声的支撑。
质询环节开始。问题一个接一个,尖锐而直接,直指当年侧写结论的核心依据和可能存在的逻辑漏洞。尤其是关于对首脑人物性格、背景和组织能力的推断,在“替罪羊”可能性被提出的前提下,遭到了最严厉的质疑。
蔺才离始终冷静应对。他的声音平稳,条理清晰,引经据典,逐一回应着质疑。他承认在信息受限的情况下,侧写存在局限性,但也坚定地捍卫了自己当年基于已有证据做出的、符合逻辑的推理过程。他甚至当场展示了这两天复查中发现的一些当年未被重视的微小矛盾点,指出这些矛盾点恰恰可能佐证了存在更高层级策划者的可能性。
他的专业、冷静和严谨,让在座的不少评审微微颔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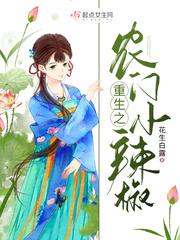

![[快穿]让反派后继有人吧!](/img/7543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