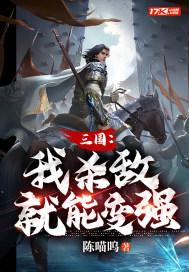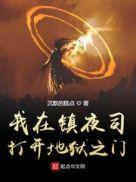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大哥别卷了,你都卷成汉中祖了 > 第187章 刘备洛阳伐谋淮南弟称号求追订求月票(第2页)
第187章 刘备洛阳伐谋淮南弟称号求追订求月票(第2页)
“可若天下皆盲,只剩一人清醒呢?”
“那便由那一人摇铃。”刘珩取出一枚小小的青铜片,正是当年铜铃残骸中最完整的一角,“我会把它交给那位少年。将来无论谁妄图重启轮回,只要这铃声响起,便是心灯未灭的证明。”
赵广久久无言,终是深深一拜,退出房门。
次日黎明,刘珩轻装简行,仅带两名仆从,悄然出城。马蹄踏过春泥,惊起林间宿鸟。行至江畔渡口,忽见一人独立舟头,素袍长袖,手持竹简。
竟是谯周。
这位昔日劝谏刘备称帝、后又屡次反对北伐的老学士,如今须发皆白,神情却比往日平和许多。见刘珩到来,他拱手道:“公子此去南中,可是为了断绝最后一丝复燃之火?”
“正是。”刘珩还礼,“先生以为如何?”
谯周仰望东方晨曦,缓缓道:“昔年我常说‘天命不可违’,故谏先主勿兴无义之师。可如今我才明白,所谓天命,不过是强者编织的谎言,用来束缚弱者的枷锁。你毁承命台,非逆天,而是还天下以选择之权。”
他顿了顿,从怀中取出一卷帛书:“这是我近年所撰《纪命篇》,论述历代所谓‘真命天子’皆由权臣塑造,民心易惑,史笔可篡。愿赠予公子,望传之后世。”
刘珩郑重接过,收入行囊。
舟行江上,水波荡漾。两岸青山徐徐后退,如同过往岁月一一告别。途中经过一处村落,正值村学开课,孩子们齐声朗读《孝经》。声音清脆,穿透晨雾。
刘珩驻足倾听,忽然听见其中夹杂一句陌生诗句:
“凤凰燃尽处,春风拂旧篱。
不拜天上客,但敬种田人。”
他心头一震。
这是从未流传过的诗,却道尽了这场斗争的真谛。
抵达南中已是七日后。那少年已在当地私塾就读半月,性情温顺,聪慧好学,已能背诵《千字文》,还会帮邻居老翁劈柴挑水。见到刘珩,他并未跪拜,只是恭敬行礼,唤了一声“先生”。
刘珩点头,将那枚铜铃残片交到他手中:“从今往后,你不必做任何人期待的模样。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全由你自己决定。”
少年握紧铜片,眼中泛起微光:“那……我可以做个教书先生吗?”
“当然可以。”刘珩笑了,“而且,你会是个很好的老师。”
当夜,山风穿堂,烛火摇曳。刘珩坐在院中,望着满天星斗,忽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
这些年,他背负太多:兄长的责任、赤凰的宿命、母亲的遗愿、丞相的托付……他曾以为,唯有完成这一切,才算不负此生。可现在他明白了,真正的解脱,不是完成使命,而是终于可以问一句:**我自己想要什么?**
他想回家。
不是回成都的府邸,也不是回当年战火纷飞的军营,而是回到那个最原始的记忆里??母亲还在厨房煮羹汤,父亲教他写字,阿斗趴在窗台上数星星,笑着说:“哥,你说以后我们会变成英雄吗?”
那样的家,早已不在。
可他知道,那样的日子,正在无数平凡人家中静静延续。
五月二十,晴。
刘珩启程返程。途经犍为郡时,接到快马加急文书:陛下刘禅??不对,应说是**阿斗化身的天地之律**??最后一次显迹于武侯祠上空。夜半时分,一道金光自祠堂屋顶升起,融入北斗第六星,随即消散无形。
这意味着,连那一丝残留的意识也已归于天地,彻底完成了它的使命。
从此世间再无赤凰,亦无救世主。
只有春耕秋收,万家灯火。
六月初一,刘珩回到成都。
他没有再去丞相府,也没有见任何官员。而是径直走入城西一座废弃的小庙??原是供奉赤凰的地方,如今香炉倾倒,神像倾颓。他亲手扫除尘埃,搬来一张木桌,几把竹椅,又从包袱里取出几本书:《孟子》《庄子》《诸葛治蜀要略》。
第二天清晨,便有附近孩童好奇探头。
“先生,这是学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