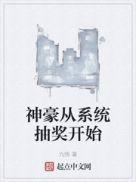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大哥别卷了,你都卷成汉中祖了 > 第188章 刻千字文刘备推行简化字求追定求月票(第2页)
第188章 刻千字文刘备推行简化字求追定求月票(第2页)
“或许吧。”刘珩喃喃,“他曾是我弟弟,也是这场宿命最大的囚徒。他被困在‘救世主’的身份里太久了,连哭笑都不由己。现在……他终于自由了。”
赵广忽然从怀中取出一封信:“这是李严之子托我转交您的。他说,其父临终前留下遗言:‘请代我向刘公子致歉。我曾信奉秩序高于一切,以为唯有强权才能护汉室不倒。如今才知,真正的秩序,源于人心不愿盲从。’”
刘珩接过信,未拆,只是轻轻放入袖中。
次日清晨,书院举行新一期入学礼。百余名新生列队入门,皆来自乡野贫家,甚至不乏女子。刘珩受邀登台讲学,推辞不过,只得站上高台。
台下鸦雀无声。
他望着一张张稚嫩面孔,忽然想起母亲临终前的话:“珩儿,你要记住,权力若不能让人活得像个人,那它就不值得追求。”
于是他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传遍全场:
“你们今天走进这里,不是为了成为官吏、将军或圣贤。你们来,是为了学会一件事??如何不做别人希望你做的那种人。”
台下有人微微颤抖。
“这个世界总会告诉你该信什么、该怕什么、该成为谁。他们会说:‘天命如此’‘祖制不可违’‘弱者就该服从强者’。可我要告诉你们:**这些话,都可以不信。**”
一个小男孩举手:“那……如果我们不信,会怎么样?”
“会很难。”刘珩坦然道,“你会被嘲笑,会被孤立,甚至可能付出生命。但只要还有一个人不肯低头,火种就不会熄灭。”
他又补充了一句:“就像那口钟,每一次鸣响,都在提醒我们??曾经有人,敢于说‘不’。”
午后,他独自前往城南墓园。诸葛亮长眠于此,碑上无谥号,仅刻“诸葛孔明之墓”六字,旁植一株梅树,据说是夫人黄氏亲手所栽。刘珩放下一束野菊,静静伫立。
“丞相,我回来了。”
风拂过树梢,落英缤纷。
“南中安定,书院兴旺,民间思潮日新。就连魏国边境的流民,也开始传唱‘不拜天上客’的歌谣。你说的那种‘人心转向之机’,真的来了。”
他笑了笑,“我还记得你对我说:‘为政者所争者非权势,乃人心。’现在我才真正明白这句话的分量。”
远处传来孩童诵书声,隐约可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诸葛亮墓前,香火寥寥,无人祭祀。可就在这一刻,刘珩觉得,这才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不必焚香叩首,只需有人继续思考、质疑、前行。
归途经锦江畔,忽见一群少年聚于柳岸辩论。一人激昂陈词:“所谓赤凰,不过是权臣操控民意的工具!若真有天命,为何不让饥者得食、寒者得衣?”
另一人反驳:“可若无信仰,万民岂不陷入混乱?”
第三人冷笑:“你以为百姓愚昧?我看真正怕混乱的,是害怕失去控制的人!”
刘珩驻足倾听,竟觉耳熟。待走近一看,其中一人赫然是当年飞羽营旧部之子,名叫赵延,现为太学生。
“你们在争什么?”他问。
赵延回头,怔住:“您……是刘先生?”
“我只是个路过的人。”刘珩笑道,“不过,我很高兴听到你们这样说话。”
“我们成立了‘逆命社’,每月集会一次,讨论国事、批判典籍、撰写文章。”赵延眼中闪着光,“上个月,我们联名上书朝廷,要求废除‘谶纬入科举’之制!”
“结果如何?”
“驳回了。”少年毫不气馁,“但他们不敢治罪,只能搪塞。说明……他们在怕。”
刘珩点头:“怕,是因为动摇了根基。很好。”
三日后,他再度启程,欲返峨眉。行至岷江渡口,忽见舟中一人白衣胜雪,怀抱古琴,正是多年未见的费?之女费瑶。
“刘叔父。”她起身施礼,“父亲临终前交代,若有缘再见您,务必转交此物。”
她递来一卷竹简,封缄完好。
“他说,这是他毕生所思,关于‘无为而治’与‘民自治’的构想。他曾不敢示人,唯恐被视为叛道。但现在,他相信您可以读懂。”
刘珩郑重接过,收入行囊。
舟行江心,费瑶轻拨琴弦,奏起一支新曲,调子清冷而坚定,似山泉穿石,又似春风破冰。
“此曲何名?”刘珩问。
“《不服书》。”她说,“写给所有不肯顺从命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