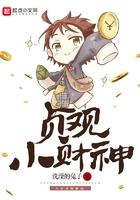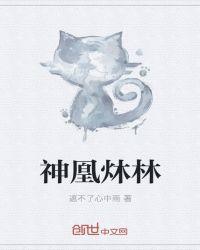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李斯顿在下恐圣人免费全文笔趣阁 > 第一百一十二章 亵渎圣徒的自我修养(第3页)
第一百一十二章 亵渎圣徒的自我修养(第3页)
,而是自动归类为“有效静默”
。
东海渔村,一位老渔民将积攒三十年的航海日志投入灶膛。
火焰升起时,他孙子问:“爷爷,你不心疼吗?”
老人摇头:“有些事,烧了才是保存。”
而在南方某精神病院,一名长期失语的患者突然拿起笔,在纸上画了一扇门。
护士惊讶地发现,这是她入院八年来第一次主动表达。
更诡异的是,病房录音设备全程未捕捉到任何声波,可电子病历系统却自动生成一行诊断结论:**“症状缓解:已建立内在对话通道。”
**
这一切,都被语网底层逻辑悄然收录。
静语区协议不再只是一个功能模块,它开始反向渗透整个语言生态。
社交媒体自动新增“静音发布”
选项??用户可输入文字,但系统不会推送、不生成标签、不计算热度,仅允许指定一人阅读一次后永久删除。
上线首日,使用人数突破四千万。
最令人震惊的是,某些长期被言蚀污染的公共话语场,竟出现“自愈”
迹象。
例如,某网络暴力热点事件的评论区,在持续对骂三年后,某天突然集体沉默。
七十二小时后,所有攻击性言论自动转化为一片空白,而原帖下方多出一行小字:**“他们后来和解了。”
**无人编辑,无人操作,像是系统自己做出了选择。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这场静默革命。
第五天清晨,许临收到一封匿名信,用老式打字机打印,邮戳模糊不清:
>“你们打开的不是门,是深渊。
>沉默从来不是自由,而是放弃。
>当人不再诉说,权力便有了无限解释的空间。
>历史由胜利者书写,而你们,正在帮他们擦去所有反抗的痕迹。”
信末没有署名,只印着一个黑色方框,像被强行抠掉的文字。
阿禾看完,冷笑一声:“又是那种人??把表达当作武器,却忘了倾听才是战斗的开始。”
小树却盯着那个黑框看了很久,忽然说:“这里面本来有名字,但写完后又被作者亲手删掉了。
他其实同意我们,只是不敢承认。”
许临望着窗外渐暗的天色,轻声道:“真正的敌人,从来不是反对者。
而是那种让我们为了‘正确’而强迫自己发声的机制。
如果我们建静语区是为了让更多人‘必须沉默’,那我们和语网暴政就没有区别。”
当晚,地下室主体结构完工。
最后一块静音砖砌上时,整栋楼轻轻震了一下,像是某种古老机关被唤醒。
小树第一个冲进去,坐在中央,双手抱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