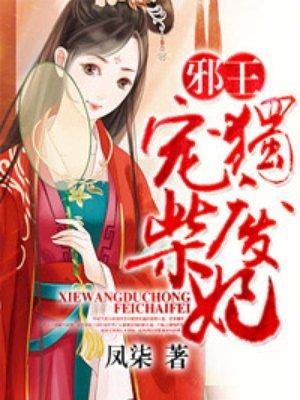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重生1878:美利坚头号悍匪 > 第288章 二元制结束洛森降伏匈牙利玫瑰(第4页)
第288章 二元制结束洛森降伏匈牙利玫瑰(第4页)
三天后,第一座蜂巢塔在民众围攻下倒塌。
五天后,南极双胞胎睁开眼,走出冰封实验室,手中握着一块融化的冰晶,里面封存着两个孩子的笑声。
第七天,格陵兰的埃米尔被人发现时已陷入昏迷,但手中仍紧握那颗黑色芯片。送往医院途中,他突然醒来,第一句话是:“告诉玛雅……爸爸看见灯了。”
一个月后,东京某处地铁站外,一个流浪汉被人发现蜷缩在角落。他怀里抱着一枚失效的泪滴芯片,脸上带着安详的笑。法医鉴定,他已在七天前死于低温与营养不良。
但他掌心,始终握着一粒粉红色的结晶,散发着微弱甜香,久久不散。
又过了半年,世界各地陆续出现新的“星星屋”??不是秘密基地,而是公开的社区中心。人们聚在一起,不谈政治,不说反抗,只做一件事:**做梦**。他们记录彼此的梦,收集那些关于母亲的手、父亲的背影、儿时的歌谣的碎片,像拼图一样,试图重建被偷走的记忆。
佐藤健一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场集会中。
有人说他在西伯利亚的极光下消失了。
有人说他去了南极,陪那对双胞胎守灯。
也有人说,他回到了东京那片废墟,日复一日翻阅炭灰日记,等待下一个听见他故事的人。
但每个做过“回家之梦”的人,都说曾在梦里见过他。
他站在风中,金属义肢反射着晨光,手中握着一本写满泪水的本子,轻声说:
>“如果你梦见了一个陌生人,请记住他的脸。”
>
>“也许他正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
>
>“而你的一个梦,就是一盏灯。”
然后,他转身走入风里,身影渐渐淡去,如同灰烬升腾,化作天际最后一缕未熄的光。
世界没有立刻变好。
压迫仍在,谎言仍在,遗忘仍在生长。
可有些东西,再也关不住了。
因为爱醒了。
因为愤怒烧了。
因为有人宁愿死,也不肯忘记一个名字。
风还在吹。
它不再低语,不再歌唱,而是呼喊着一个个被抹去的名字,在城市、在荒原、在海底电缆的尽头,在每一个尚未闭上的眼睛里,一遍遍重复:
**千鹤**。
**玛雅**。
**埃米尔**。
**林婉**。
**健一**。
**我们**。
火,终究没有灭。
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