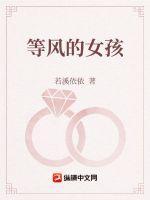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乡野村夫和落魄公子 > 我绝不放手(第1页)
我绝不放手(第1页)
苗青臻凝视着楼晟那双不见半分玩笑的眼眸,那里面只有一片沉甸甸的、近乎破釜沉舟的认真。他喉结微动,声音干涩:“……你说真的?”
楼晟下颌线绷紧,重重地点头。
苗青臻倏然起身,只留下一句“你自己洗吧”,便转身绕过屏风,脚步声渐行渐远。
楼晟望着那空荡荡的门口,眸底翻涌的光彻底寂灭,只剩下深不见底的黯淡。
先帝驾崩的哀恸如同灰色幔帐,沉沉笼罩着整个上京城。
往日觥筹交错、喧嚣鼎沸的酒楼如今门庭冷落,连街边小贩守着摊位,吆喝声也不复往日大,秦楼楚馆的姑娘们也换上了素净的黑纱,不再倚门卖笑。
恪宁帝的谥号,恰如其分地总结了他的一生,早年算得上克己奉公,守着祖宗法度,无功无过地维系着王朝运转;晚年虽沉溺于长生虚妄,却也未曾酿成动摇国本的滔天大祸。
百姓们缅怀着旧时代的终结,同时对着那位年仅六岁、龙椅上尚且坐不稳的新君,充满未知的忧虑。
李渊和的结局是流放。目的地是西南那片瘴疠横行、毒虫滋生的蛮荒之地。能否活着抵达都是未知数。
他的岳家被官兵查抄,家产尽数充公,同样被判了流刑,树倒猢狲散。
押送出城那日,囚车行经街道,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百姓们围拢过来,窃窃私语声。
“九皇子平日里那样谦和一个人,怎会做出弑兄造反的事来?”
“天家的事,谁说得准呢?那把椅子只有一个,亲兄弟也得拼个你死我活啊。”
李渊和坐在马车里,保留了皇室子弟最后的体面,未上枷锁,只一身粗布素衣。头发散乱,面容枯槁,昔日的温润气度荡然无存。
马车在或惋惜、或好奇、或麻木的目光中缓缓前行,押送官员面色冷硬,目不斜视。
队伍渐次驶过街巷,终于融入城外官道的尘土之中。
行出十余里,前方忽见数人拦路。
为首一名男子身着墨色锦袍,身姿挺拔,气度不凡,正是楼晟。身旁随从上前,向押送官员打了个手势。
官员急忙下马,拱手行礼,语气恭敬带着疑惑:“下官奉命押送罪人流放,楼大人此番是……”
楼晟因护驾有功,新帝登基后便赐下爵位,如今权势正盛,无人敢怠慢。
他唇角牵起一抹极淡的弧度:“无意耽搁诸位公务,只是受故人所托,需与车里这位说两句话,片刻即好。”
几名押送官员交换了眼色,彼此心照不宣。为首者侧身让开一步,赔着笑道:“大人请便。”
马车简陋,连个遮挡的布帘都没有,只有粗陋的木栏将内外隔开。
李渊和静坐在颠簸的车厢里。
他抬起头,一个戴着玄色面具的人不知何时已立在车外,李渊和微微一怔。
车外的人抬手,指尖扣住面具边缘,缓缓将其取下。
面具下露出的,是那张李渊和熟悉到骨子里、又遥远得如同前尘旧梦的脸。
一时间,谁都没有开口,只余下风穿过田野的微响。
李渊几乎是立刻狼狈地别开了脸,低下头去。眼眶不受控制地泛起酸涩的热意,他不想让对方看见自己此刻蓬头垢面、一身潦倒的囚徒模样。
“你这次选对了。”
苗青臻没有回应这句话,只是从怀中取出一个物件,透过木栏的缝隙递了过去。那是一块已经碎裂、又被仔细拼接黏合起来的玉章,断口处还留着清晰的痕迹。
“这个还给你,此去,一路平安。”
苗青臻自己也说不清为何非要来送这一程。
话已说完,他不再停留,转身便走,将李渊和独自留在那方狭小、颠簸的移动囚笼里。
李渊和的手指触到那冰凉碎玉,指尖猛地一颤。他摩挲着玉面上那个清晰的“和”字,这是他当年盛怒之下亲手摔碎的信印,没想到,竟是被苗青臻一片片捡起,珍藏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