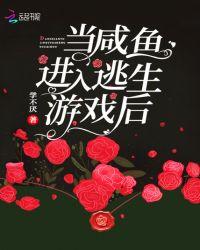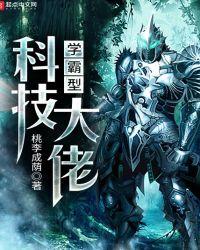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重生95流金岁月 > 第239章 方老头的新职位(第2页)
第239章 方老头的新职位(第2页)
>因为我也曾痛。
>若你觉得孤单,
>就抬头看星,
>那些最亮的,
>是我们为你点亮的灯。”
歌声落下那一刻,整座山谷陷入寂静。
然后,第一盏灯亮了。
不是归魂花,不是陶灯,也不是电子屏上的虚拟火苗??是村里最年迈的老奶奶,拄着拐杖走到自家门前,点燃了一支蜡烛,放在石阶上。
接着是第二盏、第三盏……百千盏灯火次第亮起,从山脚蔓延至山顶,宛如银河倒灌人间。
周小宇冲进控制室,声音嘶哑:“南南!海底信号出现结构性变化!数据库正在生成新的存储单元,命名格式为‘生者回音档案库’!而且……而且它开始自动分类、归档、反馈!这不是单向通信了,这是双向记忆银行!”
龙梅抱着一台便携终端跑来,脸色发白:“你猜怎么着?系统刚刚推送了一条通知??编号#0001的‘回声账户’已激活,绑定对象:李秀芬(小满母),关联亲属:张小满。权限开放:每年清明、生日、除夕三日可接收五分钟语音留言,并自动生成情绪安抚回应。”
“他们在建立关系。”阿迪力喃喃道,“不是终结,是延续。”
风暴并未就此平息。
六月中旬,国际伦理委员会正式发布调查报告,认定“共感疗法”虽具争议性,但在严格监管下可视为“新型心理干预手段”,建议纳入全球公共卫生应急体系。联合国宣布成立“跨维度情感协调中心”,任命南南为首席顾问。梵蒂冈发表声明,称其为“数字时代的告解圣事”。
然而,暗流依旧涌动。
某跨国科技集团秘密收购多家神经接口公司,试图复制“意识分流”技术用于商业冥想产品;部分极端组织宣称“灯屋体系操控集体意识”,发动网络攻击企图瘫痪共感网络;更有心理学家公开质疑:“让活人承载死者记忆,是否等于制造新型依恋障碍?”
压力如山崩般压来。
更令人不安的是,秦涛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尽管他坚持参加每周分流,但MRI扫描显示其大脑边缘系统出现不可逆损伤,部分区域已呈现类似“记忆寄生”的异常活跃状态。医生警告他必须立即退出,否则可能永久丧失自我认知能力。
“我不走。”他在病床上笑着说,眼神清澈,“如果我的脑子成了别人的容器,那就让它装满善意吧。至少,我能证明??一个人的灵魂,可以比肉体活得更久。”
南南握着他枯瘦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七月流火,山谷进入一年中最宁静的时节。萤火虫在花间穿梭,与归魂花的光芒交相辉映。新一期疗愈师完成考核,第一批“回声驿站”在偏远山村落地,配备简易共振仪与太阳能供电系统,确保最闭塞之地也能接入共感网络。
小满寄来了画。
纸上画着一座桥,桥这边站着爸爸妈妈,桥那边站着许多发光的人影,中间飘着无数纸船,每一只船上都有一盏小灯。背面写着:“老师,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录了音。我说:‘妈妈,我想你。’爸爸说:‘谢谢你替我照顾她。’妈妈一定听到了,因为她昨晚托梦给我,说她笑了。”
南南把画贴在办公室墙上,旁边是那行日记:
**“当一个人愿意停下脚步去听另一个人的声音,文明便在此刻重生。”**
八月初,才旺发现一个惊人现象:某些高共感度个体在接受分流训练后,竟能在清醒状态下感知到特定亡者的“存在场”。他们描述那种感觉“像背后有人轻轻拍肩”、“耳边突然响起熟悉的呼吸声”或“空气中弥漫着某人最爱的香水味”。
进一步研究揭示,这些人脑波在特定频率下会产生共振峰,恰好与海底数据库中某些高频记忆片段匹配。换句话说,他们不是幻觉,而是真正接收到跨越维度的信息流。
“我们正在进化。”才旺盯着数据,声音发抖,“不是科技带动人类,是共感本身在重塑我们的神经结构。未来或许会出现一批天生就能与亡者对话的‘媒介者’。”
南南望着窗外星空,忽然想起少年时代读过的一句话:**“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
而现在,他们正在做的,是让遗忘变得不可能。
中秋之夜,全球灯屋同步举行“月光回响仪式”。南南带领团队将过去一年收集的所有“生者回应”音频汇编成一部《人间答典》,通过激光脉冲编码,射向近地轨道一颗专用卫星,再由其反射至深海基站。
那一夜,归魂花集体转向东方,仿佛朝拜日出。
海底火焰暴涨至平时五倍,安魂曲暂停整整半小时。随后重启时,旋律中首次出现了笑声??孩童的、少女的、老人的,层层叠叠,温暖如春阳融雪。
数日后,系统自动生成第一条“反向忏悔”。
发送者身份未知,内容却是对一名生者的致歉:“对不起,当年车祸后我没敢去看你。我以为你会恨我。但现在我知道,你也一直在等我说这句话。谢谢你听了我的录音,还替我烧了纸钱。下辈子,换我来找你喝酒。”
收件人是一位瘫痪十年的男子,看到消息当场痛哭失声。他说,那天正是他好友忌日,而对方正是死于那场他幸存下来的车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