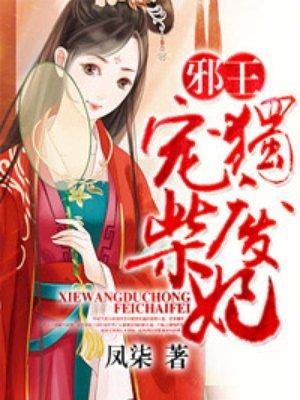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极品家丁之死灰复燃 > 第10章(第8页)
第10章(第8页)
自己竟然被自己的父亲亲手给送到了敌人手中!
赵康宁的手猛地攫住她的下巴,力道大得几乎要捏碎骨骼。
他贴近她耳畔,声音低得如同毒蛇吐信:“徐相国已应允了。徐小姐这番”苦心欺瞒“……本世子,定会好好”报答“。”
下一秒,天旋地转。
脊椎重重撞上冰冷的青砖地,闷响与剧痛同时炸开。
视野昏暗的刹那,她听见绸缎撕裂的刺耳声响,混杂着父亲远去的、沉重的脚步声,一步步,踏碎了她对这个世界最后的信任。
黑暗吞没一切之前,她最后看见的,是赵康宁那双映着烛火、燃烧着报复与欲望的猩红眼眸。
……
烛火在紫铜灯台上不安地跳动,将两道拉长的影子投在满墙书架上。
赵康宁在方寸之地反复踱步,锦袍下摆沾着的香灰与血渍随着动作簌簌飘落。
他双眼布满血丝,额角青筋隐隐搏动,整个人像一头困在笼中的受伤猛兽。
相反,徐渭端坐在黄花梨圈椅中,手持一只定窑白瓷茶盏,慢条斯理地撇着浮沫。氤氲茶烟后,老人面色平静如古井,连眉毛都未曾动一下。
“功亏一篑!”赵康宁猛地止步,一掌拍在紫檀书案上,震得笔架乱颤,“折了我许多死士,多年经营毁于一旦!如今我形迹已露,秦仙儿封城锁户,掘地三尺也要将我挖出来——”他声音嘶哑,透出几分穷途末路的狰狞,“莫说东山再起,眼下能否脱身都是未知!待那肖青璇产下林三子嗣,他地位愈固,我……我便再无机会了!”
徐渭将茶盏轻轻搁在案上,盏底与木面相触,发出极轻的“嗒”一声。
他抬眼,目光穿过摇曳的烛光:“世子此言差矣。祸福相倚,危中藏机。老朽看来,此番未必没有翻盘之隙。”
赵康宁霍然转身,疾步趋前,深吸一口气,竟对着徐渭弯腰一揖:“请相国赐教!”
“林三封城,必不能持久。”徐渭语速平缓,“京城百万生灵,商贾往来,粮秣输运,岂容长久断绝?老朽料定,不出七日,城门必开。况且——”他顿了顿,“老夫未曾与侯越白有所联系,徐芷晴更乃林三内眷,纵使顺藤摸瓜,也摸不到徐府头上。世子在此,暂且安全。”
赵康宁眉头紧锁:“即便解禁,也必外松内紧……”
“所以老朽为世子谋上、中、下三策。”徐渭截断他的话,枯瘦的手指在案上虚虚一点,“上策,直取枢要。大华承平数十载,民心所向,非向林三,实向皇权。林三之所以势大,全仗”驸马“二字。若世子能深入禁宫,面见圣上,陈说林三僭越之迹、不臣之心……只要陛下信你三分,乾坤便可逆转。”
赵康宁沉吟:“皇宫禁卫皆在林三掌握,如何进得?纵使进去,怕也是羊入虎口。”
“那便听中策。”徐渭不疾不徐,“若不能得圣心,便取实权。军中,李泰坐镇边关,与老朽有旧;财权,江东洛敏富可敌国,早向世子暗递橄榄枝。军政财三权若得其二,何愁林三不俯首?”他啜了口茶,眼底掠过一丝幽光,“只是……调动边军需出城传令。如今朝堂经侯越白一案,人人自危,谁能、谁敢为世子冒险出城?此节,需世子自行斟酌。”
边军入京……赵康宁脑中闪过史书上那些血腥旧事,心跳骤然加速。他稳住呼吸:“下策又如何?”
“下策,便是重走旧路。”徐渭放下茶盏,声音微沉,“寻机脱身,蛰伏待时,再谋刺杀。林三一死,树倒猢狲散。然此策最难——如今敌暗我明,林三经此一役必加倍防范,更有宁雨昔这等绝世高手贴身相护,得手之机,渺茫矣。故为下策。”
房中一时寂静,唯闻灯花哔剥。
赵康宁立在原地,面色变幻不定。三策皆险,如走钢丝,但确非绝路。他眼中颓色渐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孤注一掷的狠厉。
“如此……康宁便叨扰相国七日,静待城门重开。”他忽然转头,目光投向书房内侧一扇紫檀木屏风。
素绢屏面后,隐约透出一道被绳索缚住的、曲线惊心动魄的女子轮廓。
她侧卧于榻,口中似被布帛堵塞,唯有极压抑的、幼兽般的呜咽断续传来。
赵康宁嘴角扯出一个冰冷的弧度,声音低了下去:“这七日闲暇……相国若是有意旁观,康宁,不介意。”
徐渭垂眸,专注地看着杯中沉浮的茶叶,仿佛未曾听见。
烛火猛地一跳,将屏风上那道挣扎的剪影,投得愈发扭曲、漫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