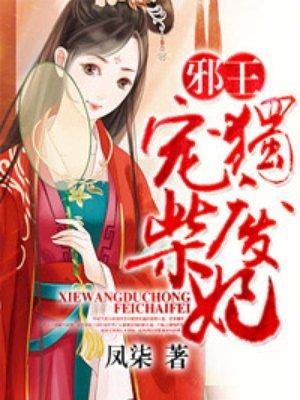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帝台春暖 > 默契(第3页)
默契(第3页)
大梁境内武器管控甚严,即便数十年前门派林立之时,江湖中人也多习刀剑,用枪者,几乎尽是兵士。
加之此人来自兴京,十年前曾被烧伤,这些关键词一一重叠,让人不免多想。
司徒靖紧紧蹙起眉头。
“我曾听祖父说起,十年前宁王自焚而死,尸首难辨,而他的贴身影卫却趁乱逃出,不知所踪,于是便试着将那人当年的模样画出,你可将此画像传于兴京,或可有助于探得此人身份。至于付巡按那里……方才在义庄时,我不知他是敌是友,便不敢贸然将此法说与他听,眼下我只信你一人,是否要将这画像拿给他,全凭你自己的心意。”
饶是司徒靖早知她于书画一道是得泽甫先生的真传,也没想到她竟真能仅凭一张毁过容的脸,就画出此人年轻时的肖像来。
见他瞠目,江楚禾有些得意。
“人的五官往往是靠颅骨形状来制约,同时又受年龄、肥瘦和男女之别的影响,其中变数颇多。我也是凭着昨晚验尸时的观察和此前多年的经验绘制,不敢说同那贼人一模一样,但七八分相似还是没跑的。”
司徒靖难掩钦佩之色,他起身作揖,道:“多谢江九娘子。”
见他这般郑重,江楚禾不禁失笑:“你倒不必同我客气,此人面容被毁已有十年之久,我也不知还能不能借此找着清楚他底细的人,恐怕还得你差人多费心思。”
说罢,她拿起药箱,准备出门。
“稍后我先去钱媪那儿瞧瞧,若取虫之法确实可行,或可顺利了结此番人祸,也不枉咱这一宿的折腾。”
司徒靖颔首,正欲对她再加叮嘱,可话到嘴边却有些迟疑。
医者仁心,向来光明磊落,他若劝其遮掩,或许在她看来,会觉得不够坦荡。
见他似有迟疑,江楚禾了然一笑,“你放心,在医治时我会寻些由头屏退左右,在用麻药让患者沉入梦中后再为其取虫。至于针刺痕迹,可以‘放血疗法’的说法应付过去,必不会让百姓知晓毒虫之事,也免得引起恐慌。”
两人的默契再次得到印证。
司徒靖压下心中那股难以名状的情绪,趋步上前,道:“我陪你去。”
“不必!”江楚禾断然拒绝,“瞧病这事儿你又不能代劳,陪我跑一趟也是白费工夫,倒不如将心思花在如何探得这黑衣人的身份上面。”
“可此人的同伙仍不知下落……”
“你就放心吧!昨夜付巡按差人追了半天,那伙贼人好不容易才跑脱,眼下若再生事端,岂非自找麻烦?”
此言不假,但他仍不放心。
“你或许不知,我曾亲眼看过李全的尸身,其肉痿之状与此番患病者确实相近,而王富已在狱中莫名丧命,可见此案背后另有阴谋,且与疫案相关。你曾蒙冤,眼下又在协助官府治疫,我怕歹人会暗中使坏,对你不利。”
他此言本意是劝江楚禾答允自己同行,不想她得知王富已死,第一反应却是关心旁人:“王富死了?那阿姎怎么样?”
“阿姎同王富并不亲近,想来无事,而且……付巡按今日会差人去黄家请阿姎问话,想必不要多久,她便会在州府衙门了。”
“也是……”想起上回见到阿姎,她并未因王富入狱而生出一丝阴霾,江楚禾略微宽心,她抓起药箱,急急走出几步,复又折返回来,正色道:“既然李全一案与这场疫病有关,那说明幕后之人准备多时,恐怕所谋甚大,你更要顾着大事,切莫因我分心。”
司徒靖只得颔首同意。
“你放心,我能保全自己,眼下当务之急,一是尽快寻得贼人下落,二是确认治愈方法,
我这就赶紧去钱媪家,待确认针刺取虫之法确有效果,还要去州府衙门向付巡按复命,届时没准还能碰见阿姎。”
江楚禾所料不错,不过几个时辰之后,她便在公廨顺利见到阿姎,但后者的状态却是让她大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