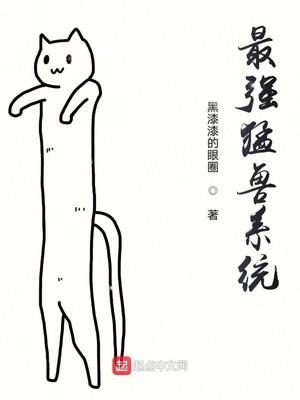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碧琉璃 > 第15章(第2页)
第15章(第2页)
织花地毯,雕刻的墙壁,绛红床被,玫色纱幔,悬挂的黄金吊灯,火焰炙热明亮,烧得如一颗泪,悠悠地,将落未落。
哗一声,有什么落在窗台。
当、当,敲两下,哪只迷糊的隼?
侧目望过,却是一位熟悉的少女,身后金翼挥动,热烈的红眸眯起,沐着月色。
拱形的窗户最适宜,因她本身是一副绚丽的油画,它便成嵌在她周身的金框。
下刻,画中人动了。
唇角微勾,轻笑一声。
“阿卿是在等我?”
卿芷望着她,又一次,呆呆不知言语。
并非那双洒金羽翼,而是靖川。
她想,原来这就是朝思暮想的滋味,伴随得愿以偿的欢欣袭来时,才知道上一刻的落寞是想念。
她下意识往前,张开双臂;少女从画里轻巧跳出,落进她迎她的怀抱。
烫得惊人。
好像刚从浴池出来似的……身上浸透了芬芳,还有沙尘干燥的气味。
她执意埋进靖川的发间,乳香、玫瑰花、羽毛的甜香。
蓬松的太阳气味。
这才是她的味道。
松了怀抱,靖川像乏了,几步拨开床幔,蹬了一双金鞋,往卿芷床上一躺。
卿芷为她拾好鞋,摆整齐,才坐在床边。
她慵懒地趴在卿芷整理得一尘不染的床上,稍稍滚一圈,规整的被子也乱了。
像只猫撒欢,一躺,不是她的也要属于她。占山为王。
“教我写字。”靖川翻了个身,手枕在自己脑后。
她的长裙因屈膝往上提了些,露出洁白的小腿,脚踝上缠着细密的金链。
金链……卿芷望着那根链子。
说来靖川生得实在是白。
没有一丝西域人被黄沙常年洗磨的铜色,皮肤细嫩,眉眼浓艳却又精巧,尤其一双眼,睫毛浓密,眯起来时,妩媚多情。
她说:“夜了,该歇息了。”
靖川望定她,笑意有些玩味,眸光冷下来:“你在管教我?”
卿芷像察觉不到她的威胁——她本来也不是那些悉听尊便的臣民,仍坚持道:“现在不合适。”
“耍赖。”靖川见她不吃这套,轻哼一声,“我满足了你的愿望,你却拒绝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