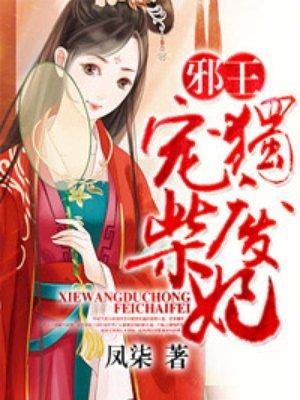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星星是冰冷的玩具(全二册) > 4(第5页)
4(第5页)
他的话音愈来愈低。他要走了。而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不知道怎么才能告诉他我所坚信的东西,告诉他存在救赎,告诉他什么才是我们世界唯一的、永恒不变的船锚……
“有人在等你回去,克洛斯。你的妻子在等你。如果你还能坚持下去,那她也能坚持到你回去。”
“有必要坚持吗?”
“你就是软弱!”我朝他喊,“好好听我说!我不知道对你来说什么才是最珍贵的,什么是无所谓的,但你要记住一件事:门就是一根线,只要有人在牵着线的一头,只要还有人在等你……”
他笑了,笑容在他支离破碎的脸上显得很滑稽。
“有人在等你,克洛斯。你要相信我!”
“不要为其他人做决定……永远不要……”
我站了起来,看向玛莎。
“我没有别的办法,”她小声说,“彼得,我开枪了……那个恶棍有力场盾……”
恶棍?
当然不是。它们只是在保护自己的世界,在保护那一小团好不容易得来的幸福。我们比它们更强,所以胜利了。天没崩,地没裂,被赠予的种子不是神话中不能被夺走的神符。它可以被夺走,别的都不重要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进入暗影的方式。
我走向已经动弹不得的蓝皮人,掰开它的手,从它指缝间抠出那块凝固的冰冷火焰。
它的身体颤抖起来,巨大的复眼中似乎还残存着意识。
“它还活着!”玛莎惊叫道,“打死它,彼得!”
蓝皮人没有抵抗,只是躺在那儿低声哀鸣。或许这就是它们的哭声。它的手指愈发牢固地攥着那颗种子,几乎快把它捏碎。
“你们到底遭遇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坚持!”我朝它咆哮起来。
它呜咽着,一点点被推向悬崖边缘,被它抓在手中的种子几乎要看不见了。
“快杀了它!”玛莎又催促了一遍。
“你能办到吗?”我粗暴地质问道,玛莎不说话了。
“需要……”外星人忽然嘟囔起来,“需要。非常。非常。需要。非常……”
断断续续的语句不是翻译的问题。我们现在能毫无障碍地理解彼此。这只是它的思维模式。它们就是这样低等的生物,跟我们相差太远。
“很糟……非常。非常。不好。不好。死亡。降临。死亡。降临……”
我可能无法理解它们的情绪,它们似乎无法用薄薄的嘴巴传达自己的意思,只能可怜兮兮地说出毫无意义的词汇,永远无法驳倒我,就像我永远无法驳倒克洛斯。而克洛斯已经永远离开了,仿生人不再扮演人类了,蓝皮人的世界也将消失……是的,我相信它们也面临着灭顶之灾,甚至可能比我们的处境还要糟糕,但那不关我的事,我必须拯救自己的地球……
至于将来那些评论我功过是非的人、那些祈求自己的罪孽得到宽恕或者可笑地对着已灭亡种族微笑的人……我很好奇,他们的悔恨或欣慰到底取决于什么?我该如何看待前方那个阳光普照的世界?该如何面对这些人脸上的表情?
如何抉择?
“给我,”我说,“给我。我们很需要它。需要。需要。”
它的手掌松开了。我拿走了那颗小小的种子。它摸上去不是冰凉的,而是有温度的……尽管只是微温。
它不是冰冷的。
这一小团柔软的火焰,就是门的胚胎。
玛莎在我背后松了口气。她伸出手把我拉了回去,低声说:
“就让它们去死吧……彼得,我们走吧……”
我没有挪动脚步。玛莎走向克洛斯,弯下腰,抱起他的身体。我用余光看到她将克洛斯拖向飞行器。
你是怎么说的,克洛斯?每个人都有自己进入暗影的方式?有的人苦苦哀求,有的人勤恳奋斗,有的人强取豪夺?不必良心不安?
我看向远方。很远很远的地方,我的后代在微笑。
“就让这一切都去死吧。”我接受了玛莎的建议。
我把种子还给了蓝皮人。
它的复眼又亮了起来,倒映出种子的火光。
“你要给我吗?还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