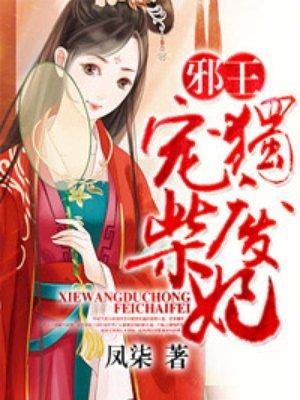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背德者 > 第三部(第3页)
第三部(第3页)
“什么也没干。”
“偷东西了吧?”
他摇头否认。
“你现在干什么?”
他又笑起来。
“哎!莫克蒂尔!你若是没什么事儿干,就陪我们去图古尔特吧。”——我突然心血**,想去图古尔特。
玛丝琳的身体状况不好,我不知道她有什么心事。那天晚上我回旅馆的时候,她紧紧依偎着我,闭着眼睛一句话不讲。她的肥袖筒抬起来时,露出了消瘦的胳臂。我抚摩着她,像哄孩子睡觉似的摇了她好长时间。她浑身颤抖,是由于情爱,由于惶恐,还是由于发烧呢?……哦!也许还来得及……难道我就不能停下来吗?——我思索并发现自己的价值:一个执迷不悟的人。——可是,我怎么开得了口,对玛丝琳说我们明天去图古尔特呢?……
现在,她在隔壁房间睡觉。月亮早已升起,此刻光华洒满平台,明亮得几乎令人惊悚。人无处躲藏。我的房间是白石板地面,月色显得尤为粲然。流光从敞着的窗户涌进来,我能看到它在我的房间里的光华和房门上的阴影。两年前,它照进来得还要远……对,正是它现在延伸到的地方——当时我夜不成寐,便起床了。我的肩头倚在这扇门扉上。还记得,棕榈也是纹丝不动……那天晚上,我读到什么话了呢?……哦!对,是基督对彼得说的话:“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我去哪里呢?我要去哪里呢?……我还没有告诉你们,我上次到那不勒斯的时候,一天又独自去了帕埃斯图姆……噢!我真想面对那些石头痛哭一场!古迹的美显得质朴、完善、明快,却遭到遗弃。艺术离我而去,我已有所感觉,但是让位给什么了呢?代替的东西不再像往昔那样呈现明快的和谐。现在我也不知道我为之效力的神秘上帝。新的上帝啊!还让我认识新的种类,意想之外的美的类型吧。
次日拂晓,我们乘驿车起程了。莫克蒂尔跟随我们,他快活得像国王。
奇加、凯菲尔多尔、姆莱耶……各站死气沉沉,走不完的路途更加死气沉沉。老实说,我原以为这些绿洲要欢快得多,不料满目石头与黄沙,继而有几簇花儿奇特的矮树丛,有时还望见暗泉滋润的几株试栽的棕榈……现在,我喜欢沙漠而不是绿洲。沙漠是光彩炫目、荣名消泯的地方,人工在此显得丑陋而可怜。现在我讨厌任何别的地方。
“您喜爱非人性。”玛丝琳说道。瞧她那自我端详的样子!那目光多么贪婪!
次日有些变天,也就是说起风了,天际发暗。玛丝琳感到很难受,黄沙灼热的空气刺激她的喉咙,强烈的光线晃花她的眼睛,怀有敌意的景物在残害她。然而,再返回去已为时太晚。过几个小时就到图古尔特了。
这次旅行的最后阶段虽然相隔很近,给我留下的印象却非常淡薄。第二天旅途的景色、我刚到图古尔特所做的事情,现在都回忆不起来了。不过,我还记得我的心情是多么急切。
上午非常冷。向晚时分,刮起了干热的西蒙风。玛丝琳由于旅途劳顿,一到达就躺下了。我本指望找一家舒适一些的旅馆,想不到客房糟透了。黄沙、曛日和苍蝇,使一切显得昏暗、肮脏而陈旧。从拂晓以来,我们几乎就没有进食,我立即吩咐备饭。可是,玛丝琳觉得没有一样可口的,任我怎么劝还是一口也咽不下去。我们随身带了茶点。这些琐事全由我承担了。晚餐将就吃几块饼干,喝杯茶,而当地水太污浊,煮的茶也不是味儿。
仁心已泯,最后还虚有其表,我在她身边一直守到天黑。陡然,我仿佛感到自己精疲力竭。灰烬的气味啊!慵懒啊!非凡努力的悲伤啊!我真不敢瞧她,深知自己的眼睛不是寻觅她的目光,而是要死死盯住她那鼻孔的黑洞。她脸上的痛苦表情令人揪心。她也不瞧我。我如同亲身触及一般感到她的惶恐。她咳得厉害,后来睡着了,但时而惊抖。
夜晚可能变天,趁着还不太晚,我要打听一下找谁想想办法,于是出门去。旅馆前面的图古尔特广场、街道,甚至气氛都非常奇特,以至我觉得不是自己看到的。过了片刻,我返回客房。玛丝琳睡得很安稳。刚才我的惊慌是多余的。在这块奇异的土地上,总以为处处有危险,这实在荒唐。我总算放下心来,便又出去了。
广场上奇异的夜间活动景色:车辆静静地来往,白斗篷悄悄地游弋,被风撕破的奇异的音乐残片,不知从何处传来。一个人朝我走过来……那是莫克蒂尔。他说他在等我,算定我还会出门。他咯咯笑了。他经常来图古尔特,非常熟悉,知道该领我到哪儿去。我任凭他把我拉走。
我们走在夜色中,进入一家摩尔咖啡馆。刚才的音乐声就是从这里传出去的。一些阿拉伯女人在跳舞——如果这种单调的移动也能称作舞蹈的话——其中一个上前拉住我的手,她是莫克蒂尔的情妇。我跟随她走,莫克蒂尔也一同陪伴。我们三人走进一间狭窄幽深的房间,里边唯一的家具就是一张床。床很矮,我们坐到上面。屋里关着一只白兔,它起初非常惊慌,后来不怕人了,过来舔莫克蒂尔的手心,有人给我们端来咖啡。喝罢,莫克蒂尔就逗兔子玩,这个女人则把我拉过去;我也不由自主,如同沉入梦乡一般。
噢!这件事我完全可以作假,或者避而不谈,然而,我的叙述若是不真实了,对我还有什么意义呢?
莫克蒂尔在那里过夜,我独自返回旅馆。夜已深了。刮起了西洛可焚风,这种风卷着沙子,虽在夜间仍然酷热,迷人眼睛,抽打双腿。突然,我归心似箭,几乎跑着回去。也许她已经醒来,也许她需要我吧?……没事儿,房间的窗户是黑的,她还在睡觉。我等着风势暂缓好开门。我悄无声息溜进黑洞洞的房间。——这是什么声响?……听不出来是她咳嗽……真的是她吗?……我点上灯……
玛丝琳半坐在**,一只瘦骨伶仃的胳膊紧紧抓住床头栏杆,支撑着半起的身子。她的床单、双手、衬衣上全是血,面颊也弄脏了;眼睛圆睁,大得可怕;她的无声比任何垂死的呼叫都更令我恐惧。我在她汗津津的脸上找一点儿地方,硬着头皮吻了一下。她的汗味一直留在我的嘴唇上。我用凉水毛巾给她擦了额头和面颊。床头下有个硬东西硌着我的脚,我弯腰拾起,正是在巴黎时她要我递给她的小念珠,刚才从她的手中滚落了。我放到她张开的手里,可是她的手一低,又让念珠滚落了。我不知如何是好,想去找人来抢救……她的手却拼命地揪住我不放。哦!难道她以为我要离开她吗?她对我说:
“噢!你总可以再等一等。”她见我要开口,立即又补充一句,“什么也不要对我讲,一切都好。”
我又拾起念珠,放到她的手里,可是她再次让它滚下去——我能说什么?实际上她是撒手丢掉的。我在她身边跪下,把她的手紧紧按在我的胸口。
她半倚在长枕上,半倚在我的肩头,任凭我拉着她的手,仿佛在打瞌睡,可是她的眼睛却睁得大大的。
过了一小时,她又坐起来,把手从我的手里抽回去,抓住自己的衬衣,把绣花边的领子撕开了。她喘不上气儿。——将近凌晨时分,又吐血了……
我这段经历向你们讲完了,还能补充什么呢?——图古尔特的法国人墓地不堪入目,一半已被黄沙吞没……我仅余的一点儿意志,全用来带她挣脱这凄凉的地方。她安息在坎塔拉她喜欢的一座私人花园的树荫下,距今不过三个月,却恍若十年了。
米歇尔久久沉默,我们也一声不响,每个人都有一种莫名的失意感。唉!我们觉得米歇尔对我们讲了他的行为,就使它变得合情合理了。在他慢条斯理解释的过程中,我们无从反驳,未置一词,未免成了他的同道,仿佛参与其谋。他一直叙述完,声音也没有颤抖,语调、动作无一表明他内心哀痛,想必他厚颜而骄矜,不肯在我们面前流露出沉痛的心情,或许他出于廉耻心,怕因自己流泪而引起我们的慨叹,还兴许他根本不痛心。至今我都难以辨别骄傲、意志、冷酷与廉耻心在他身上各占几分。过了一阵工夫,他又说道:
老实说,令我恐慌的是我依然年轻。我时常感到自己的真正生活尚未开始。现在把我从这里带走,赋予我生存的意义吧,我自己再也找不到了。我解脱了,可能如此,然而这又算什么呢?我有了这种无处使用的自由,日子反倒更难过。请相信,这并不是说我对自己的罪行厌恶了,如果你们乐于这样称呼我的行为的话。不过,我还应当向自己证明我没有僭越我的权利。
当初你们同我结识的时候,我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而今我知道正是这种信念造就真正的人,可我却丧失了。我认为应当归咎于这里的气候,令人气馁的莫过于这种持久的晴空了。在这里,无法从事任何研究,有了欲念,紧接着就要追欢逐乐。我被光灿的空间和逝去的人所包围,感到享乐近在眼前,人人都无一例外地沉湎其中。我白天睡觉,以便消磨沉闷的永昼及其难熬的空闲。瞧这些白石子,我把它们放在阴凉的地方,然后再紧紧地握在手心里,直到起镇静作用的凉意散尽。于是我再换石子,把凉意耗完的石子拿去浸凉。时间就这样过去,夜晚来临……把我从这里拉走吧,而我靠自己是办不到的。我的某部分意志已经毁损了,甚至不知道哪儿来的力量离开坎塔拉。有时我怕被我消除的东西会来报复。我希望从头做起,希望摆脱我余下的财产。瞧,这几面墙上还有盖儿。我在这儿生活几乎一无所有。一个有一半法国血统的旅店老板给我准备点食品,一个孩子早晚给我送来,好得到几苏赏钱和一点儿亲昵——就是你们进来时吓跑的那个。他特别怕生人,可是跟我一起却很温顺,像狗一样忠诚。他姐姐是乌莱德——纳伊山区人,每年冬季到君士坦丁堡向过客卖身。那姑娘长得非常漂亮,我来此地头几周,有时允许她陪我过夜。然而一天早晨,她弟弟小阿里来这儿撞见了我们两个。那孩子极为恼火,一连五天没有露面。按说,他不是不知道他姐姐是怎样生活,靠什么生活的。从前他谈起来,语气中没有表露一点儿难为情。这次难道他嫉妒了吗?——再说,这出闹剧也该收场了,因为我既有些厌烦,又怕失去阿里,自从事发之后,就再也没有让那位姑娘留宿。她也不恼,但是每次遇见我,总是笑着打趣说,我喜爱那孩子胜过喜欢她,还说主要是那孩子把我拴在这里。也许她这话有几分道理……